
標題

標題
內容
7艘漁船橫渡太平洋!硬核的廣東僑鄉史藏在這本書里
更新時間:2025-06-05 作者:影子 熊育群來源:南方雜志
2023年,作家熊育群的長篇小說《金墟》出版,講述了一個跨越百年的華僑家族故事。小說以廣東江門開平、臺山一帶的華僑歷史為背景,融入了真實的歷史事件、鮮活的人物命運,以及赤坎古鎮的風土人情。
近日,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公布了廣東省第十三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入選作品名單,《金墟》成功入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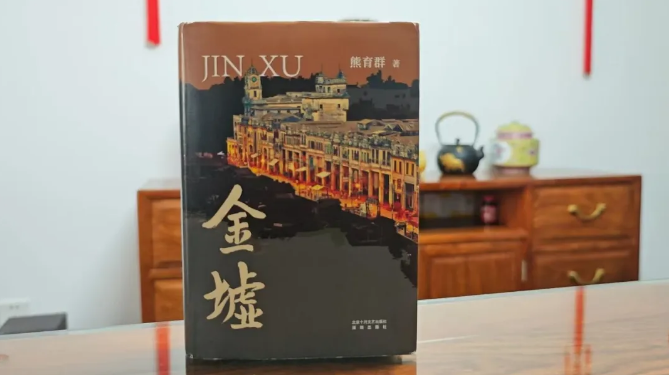
《金墟》。攝影:劉家業
該作品榮獲上榜“第七屆長篇小說年度金榜”,入選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目前正在翻譯阿拉伯文、馬來文、土耳其文、波斯文。
在文學與現實交匯的旅途中,熊育群如何用文字還原華僑奮斗史?又如何在小說創作中平衡歷史真實性與藝術想象?近日,他接受了《南方》雜志記者的專訪,分享了自己的創作心路與僑鄉文化的獨特魅力。
1
這片土地,讓我萌生寫一部大書的沖動
《南方》雜志:您是“改革開放再出發”創作活動的作者之一,當初是出于怎樣的考量,決定結合江門的華僑史來創作一部作品呢?
熊育群:這源于我與開平的不解之緣。2007年,我初訪開平,寫下散文《雙族之城》,引發熱烈反響,在《人民文學》發表,并在《新華文摘》等轉載,榮獲百花文學獎。那時,赤坎古鎮正進入征收開發階段,有人建議我寫一部長篇小說,把這段獨特的歷史記錄下來。這個想法像是一束光,點燃了我的創作激情。我意識到,廣東百余年的華僑史是中國與西方碰撞融合的生動縮影,而赤坎古鎮的兩大家族,他們與海外的千絲萬縷的聯系,與國家命運的緊密交織,正是展現這段歷史的絕佳切口。恰逢省委宣傳部、省作協正開展“改革開放再出發”深扎創作活動,我毅然報名投身其中。這期間我掛職江門市委宣傳部,在創作期間,江門市委宣傳部、開平和赤坎鎮給予了大力支持,深入基層采訪,積累素材,希望用文學的方式,讓這段歷史重現于世。

江門華僑文化豐富,圖為開平塘口鎮自力村。受訪者供圖
《南方》雜志:從掛職到創作完成,這部作品據說歷經了6年之久,您能跟我們詳細講講這段創作歷程嗎?
熊育群:在掛職之前,我就多次前往開平采訪,甚至遠赴美國,深入司徒氏等華僑家中,對華僑的生活和故事有了初步并深刻的認識。在“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深扎行動中,我掛職江門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達一年多,這期間全身心地沉浸在開平的生活中。之后,又花費了一年時間進行創作,前前后后,這部《金墟》歷經了六年的打磨。在這漫長的歲月里,我四處奔波,積累了海量的素材,為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熊育群赴美國采訪華僑。受訪者供圖
2
寫作是尋找那些被遺忘的故事
《南方》雜志:您的這部46萬字的鴻篇巨制,從早期赴美的華僑,到建設赤坎的司徒文倡,再到現代的鎮長司徒譽,構筑了一座虛實交融的敘事橋梁。您如何在歷史與虛構之間找到平衡?
熊育群:這是對作家極大的考驗。我書寫的是百余年的歷史,時間橫跨世紀,空間跨越太平洋兩岸,涉及兩大家族的興衰沉浮。從1926年赤坎古鎮的建設,到本世紀的開發,近百年的光陰流轉,四代人的命運交錯。當年的當事人大多已不在,如何讓不同時代的場景鮮活重現,成為創作的一大挑戰。
我采用紀實的風格,環境、事件、主要人物、地點皆有據可考。比如寫100年前的舊金山,不能憑空想象,必須深入史料,考證細節。同時,為了讓各時代的故事渾然一體,我塑造了十多個關鍵人物,讓他們成為連接百年歷史的紐帶。這種手法雖充滿挑戰,但也賦予作品獨特的創新張力,使小說不僅呈現風云激蕩的時代,更刻畫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折射出家族興衰、復雜人性,以及華僑愛國愛鄉的情感。這不僅是一部關于華僑的故事,更是關于中華民族家國情懷的書寫。
《南方》雜志:為了創作這部作品,您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積累了海量史實和素材。面對龐雜的信息,您是如何取舍、融合,使其服務于小說敘事的?
熊育群:首先是廣泛收集資料,開平百余年的歷史,是嶺南僑鄉歷史的縮影,也與中國近現代乃至世界歷史息息相關。我主要依托兩大途徑:一是檔案館,僑鄉文化在僑刊中有著連貫記載,百年來幾乎未曾中斷;二是歷史事件相關資料,包括書籍、口述史等,我從朋友、圖書館等各種渠道搜集而來。
有些史料的獲取甚至帶著偶然性。比如書中“吳寄”的原型厲齊,他仿佛一本活的歷史字典,對各村、各家族的人物與百年故事了然于胸。我曾與他深入交談四天四夜,光錄音就達20萬字。當地很多人對某些歷史細節已模糊,而他的講述為我填補了大量生動的細節。當然,我不會完全依賴口述,而是親自實地調查,遍訪每個村落、每處歷史遺跡,像爬百足山考察文天祥的“文山祖墓”。最終,我整理的材料累計上千萬字,采訪上百人,包括工匠、華僑老人、學者等,每個人的記憶碎片,最終交織成這部作品的歷史肌理。

熊育群爬上屋頂采訪灰塑師傅。受訪者供圖
《南方》雜志:最終定稿46萬字,那初稿、二稿經歷了怎樣的修改?
熊育群:初稿的字數與定稿相近,但二稿時幾乎進行了大幅重寫,僅保留了約五分之二,五分之三是重新創作的。整個過程經歷三稿,歷時一年。
第一稿最為艱難,龐大的素材需要梳理,而故事本身充滿戲劇性:兩大家族的競爭、華僑的命運沉浮、時代的激蕩變遷……初稿像一篇“報告文學”,過于紀實。小說不能堆砌史實,最精彩也得舍棄。二稿時,我拋開史實的束縛,用更多虛構手法,使之更具文學張力。第三稿,則完全不受拘束,只從小說要求進行潤色與創作。
表面上,這部作品紀實感很強,但其實約七成內容是虛構的。名人、地名、家族、環境、重要事件等是真實的,但主要人物與情節是虛構的。這種虛實交錯,既讓歷史有了溫度,也使故事更具穿透力更有力量。我想表達的,不只是僑鄉的百年變遷,而是如何在時間長河中,捕捉那些不能被遺忘的寶貴瞬間,它們深具現實意義。
3
小說的語言,必須帶著僑鄉的味道
《南方》雜志:您的作品對江門風物描寫細膩入微,并巧妙融入開平方言。創作時,您如何考慮這些元素的運用?
熊育群:江門是我長時間生活的地方,這片土地早已浸入我的血脈。我對它的風物有著天然的親近感,所以在創作中,我格外注重那些能夠承載地方記憶的事物,比如良溪、柑普茶、陳皮等,這些不僅是地域特色的象征,更是人們生活方式的映照。用文學去描摹這些風物,就像用畫筆為江門繪制一幅充滿溫度的風情畫。
方言更是文化的魂魄。如果不讓語言生長在它最真實的土壤里,人物的氣質、故事的底色就會失去質感。然而,使用方言并非易事。開平方言與粵語有所不同,我作為外地人,為了精準掌握,不僅查閱方言詞典,還向當地人請教,反復核實。我的原則是:方言要讓不懂的人能看懂,同時盡可能保留它的韻味。如今,許多小說趨向標準化、城市化,地方特色逐漸被沖淡,我希望通過這部作品,讓讀者感受到嶺南文化的獨特氣息。
04
文學的使命,是讓人們看見自己的文化和歷史
《南方》雜志:這部作品榮獲了一系列的榮譽,您希望通過它向讀者傳達怎樣的核心主題和精神呢?
熊育群: 這部作品承載著多個層面的主題。最核心的,是華僑的家國情懷。他們遠離故土,卻始終心系祖國,哪怕身處異鄉,依然努力反哺家鄉。這種精神,不僅僅屬于某個家族、某個地域,更是一代代華人共同的血脈傳承。
同時,我希望書中展現出的為家鄉干實事的追求能引起共鳴。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人用實際行動書寫著拼搏傳奇。他們務實、敢闖,為家鄉建設傾盡心血。我在書里描繪的,不僅是他們的日常生活,更是一種人的價值與追求。
此外,廣東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打開國門,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國進入現代國家行列……這里始終是連接世界的重要窗口。我試圖通過小說,把百年廣東的風云變遷重新展現給讀者。比如,書中寫到的那7艘9米長的漁船橫渡太平洋、抵達美國加州,這樣的壯舉在世界航海史上值得銘記。很多歷史被塵封,但它們值得被挖掘,被重新講述。
《南方》雜志:聽說您為了創作深入生活,參加當地婚禮、葬禮等。這些經歷對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熊育群:深入生活對于創作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比如,江門的婚禮從半夜就開始,我凌晨一點就起床,全程參與,親眼見證那些傳統禮俗如何在現代生活中延續。寫作時,那種場景感自然而然地流淌在文字里。
還有砌房看風水、灰塑工藝,我不僅是觀察者,更是參與者。我曾爬上屋頂,近距離看師傅如何用手中的工具雕刻出一件件精美作品。他們還手把手地教我,這種切身體驗,讓作品中的民俗描寫更有質感。
至于葬禮,那更是一種挑戰。我曾經猶豫過,但最終還是選擇走進去。只有親歷,才能真正理解生死觀念在當地人心中的分量。作品中關于葬禮的細節,許多讀者看了都深受觸動,這正是因為它們源自真實的體驗,而非憑空想象。我還將虛構的人物放置在真實的建筑環境中,通過錄像、拍照等方式詳細記錄,這樣在小說中就能營造出強烈的現場感。
《南方》雜志:您的家鄉汨羅與江門在文化上有哪些異同?這些差異對您的創作有何影響?
熊育群:這兩地雖相隔千里,但都是中原移民的血脈,都重視宗族觀念,有著強烈的歸屬感和尋根意識。這是一種中華文化的共性。
但差異也很明顯。汨羅人嗜辣,而江門飲食偏清淡;語言截然不同,生死觀更是大相徑庭。更深層次的區別在于文化氣質——湖南人更注重精神追求,江門人則更講究現實和務實。這些對比,讓我在創作時更加注重地方特色,盡量避免將個人經驗簡單移植,而是去挖掘江門文化的獨特韻味。
《南方》雜志:作品中對疍家人的描寫令人印象深刻。您能談談這部分內容與當地歷史的聯系嗎?
熊育群:疍家人長期漂泊于水上,日復一日地與江海為伴,他們的生活充滿艱辛,卻也孕育了獨特的文化。赤坎的疍家人曾參加反清復明,后漂泊大海,但與赤坎的歷史緊密相連。
赤坎的關氏家族在明代就參與西方的貿易,來到了上川島,成為了島上旺族。西方傳教士最早抵達的也是上川島。這些歷史大多已被當地人遺忘,通過我的田野調查才得以挖掘呈現,并且與海上絲綢之路等歷史緊密聯系起來,展現出地方歷史的宏大與豐富。廣東的水運、貿易、移民史,是嶺南文化的厚重底色,我希望通過文學,把這些塵封的歷史重新點亮。
《南方》雜志:您如何看待廣東文學的潛力?對未來的創作有哪些期待?
熊育群:廣東文化豐富多彩,廣府、客家、潮汕文化各具特色,歷史底蘊深厚,波瀾壯闊,其中隱藏著眾多不為人知的精彩故事,等待著作家們去挖掘。自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像華為相關事件、中美貿易戰等,廣東都處在風口浪尖。對于作家而言,只要有雄心壯志,就完全能夠創作出厚重的作品。如今,大灣區文學蓬勃發展,像黃谷柳先生的《蝦球傳》,通過方言與日常生活展現出濃郁的嶺南風味,這樣的作品就是大灣區的,從生活、環境、習俗到語言都是打通的,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大灣區文學是大有可為的,你有多大雄心壯志,你就能夠寫出多么宏大的作品來。這塊土地不缺故事,缺的是發現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