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打造“新大眾文藝”的東莞樣板
更新時間:2025-04-28 來源:南方+
“在這塊土地上,產生幻想的不是本地人,而是一個時代的闖入。虎門這個小鎮,每個世紀的到來,是時間說了算……”
今年初,《作品》雜志刊發了5萬字的長篇散文《清潔女工筆記》,引發了多方關注與討論。這些質樸自然的文字并非源于專業作家之手,而是流淌自清潔女工王瑛的筆端,記錄著她在一家售樓部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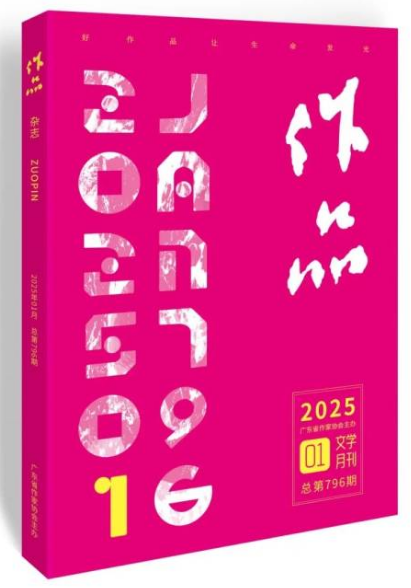
2025年第1期《作品》
《作品》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王十月鄭重地為這篇散文寫下推薦語——“她的文字既有對保潔生活的如實記錄,又有從低處的生活中生出的對星空的渴望……她的文字有著毛絨絨的生活質感,正是這質感,使得文中偶爾對星空的仰望顯得格外真切動人……”
在東莞,像王瑛這樣來自各行各業、書寫與眾不同生活經驗的作者還有很多,從燒烤店員工、石材廠工人,到街道主任、體育老師……他們一度隱沒在大眾視野之外,如今卻像一股股南粵大地深處涌現的潛流,匯聚成“新大眾文藝”的奔騰江河,為當代文學提供了新的可能和經驗。
帶著“生命印痕”的深刻寫作
時間撥回2008年。那一年,王瑛從汶川來到東莞發展,成為一名學前教育老師。退休后,她應聘到一家樓盤的售樓部當清潔女工。工作的間隙,她總是會用手機的備忘錄記錄下生活中的點滴感受,下班后再對這些內容進行修改。
后來,這些由一條條備忘錄沉淀而來的文字,被投給了《作品》雜志社,并幸運地遇到了“伯樂”。而《作品》等文學期刊之所以能成為發掘業余寫作者的重要陣地,與東莞多年前興起的打工文學潮流關系密切。

王瑛
王十月與《作品》雜志社副社長、副總編輯鄭小瓊都是東莞打工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在他們通過寫作上演命運逆轉的傳奇、實現身份的華麗轉變之后,發現和培養更多的業余寫作者便成為一種天然的使命。這一“傳幫帶”機制,正助力東莞形成良好的文學代際傳承。
與王十月發現王瑛的過程類似,鄭小瓊也發掘出溫雄珍。這位小學五年級輟學、15歲從廣西來到東莞的女性,白天擺地攤,晚上在燒烤店打工。有幾年因為丈夫出車禍受傷,孩子還小,家里的重擔壓在她一個人肩上。但生活的磨難沒有令她屈服,對文學的熱愛讓她堅持寫作,忙碌奔波、“煙熏火燎”的生活,為她的詩歌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
2015年,溫雄珍被一位文友拉進詩歌群,在這里,她得到了許多師友的耐心指導,對文學也有了新的認知。“剛開始寫詩時,還有很多錯別字,我就從認字開始。”慢慢地,溫雄珍的思路發生了轉變,“每天我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每個人背后都有故事。我就在想,怎樣把身邊的故事用文字表達出來”。
“游走在約古宗列曲的綿羊/到了晚上,把群星帶回人間”“碾碎荒漠,在原有的土地上/開出屬于我們的花朵”“沒有人能從那場炙焰中把你解救出來,除非你/找到了那把梯子……”溫雄珍的作品,既有對遼闊“遠方”的詩意想象,也有對“生命印痕”的深刻審視。
鄭小瓊留意到溫雄珍的才華,在《作品》雜志刊登了數十首她的詩歌,東莞市作協主席胡磊則以“溫熱生活中蓬勃煙火氣”為主題,為她的作品寫了數千字的評論。這種對業余寫作者的全力托舉,一直讓溫雄珍心存感激。
在為18歲的女兒寫寄語時,溫雄珍寫道:“一個人無論處在什么環境,都要努力向上,開心健康。”這是她對女兒的溫暖祝愿,也是自己多年來在東莞追逐文學夢想的心得與體會。
“這種不斷地發現、培育人才,是東莞業余寫作群體很突出的一個特點,也體現了‘新大眾文藝’強調的平等特質,城市里的每一個人都能被文學之光照耀。”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柳冬嫵評價說。
來自生活“第一現場”的沖擊力
如果說打工文學是東莞40多年來高速發展的見證,那么近年來“新大眾文藝”的寫作者及其表達的主題,早已超出了“打工”的范疇,為東莞的城市敘事注入新的色彩。
作為一個以外來人口為主的城市,東莞的人群來自五湖四海。他們帶著不同的口音、不同的記憶、不同的生活觀念來到此處,碰撞與交融時刻發生。
曾經在石材廠當工人的曾為民寫了幾百首“石頭詩”,他用“一塊風餐露宿的石頭”,記錄下自己對親情的刻骨思念:“讓我想起漂泊多年的父親/也是這樣悄悄風化/以至于,我想不起他/曾經的容顏”;賣菜為生的黃立明在凌晨的雨夜中,完成一首大氣磅礴的《世界神農》,“東方魔稻/滿世界揚花吐蕊/世界因您而安康/世界正走在告別饑饉的路上”,表達了一個普通人對“當代神農”袁隆平先生的由衷敬意。

曾為民
放眼全國,業余寫作也變得越來越普遍與流行,從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到王計兵的《趕時間的人:一個外賣員的詩》,從“奶奶作家”楊本芬的《豆子芝麻茶》到高校教師楊素秋的《世上為什么要有圖書館》……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用文字安放精神和靈魂。
“這些業余寫作者,他們用自己的肉身去感受過的、用自己的手摸過的、用自己的腳丈量過的經驗,更具有‘第一現場’的沖擊力。”中山大學教授、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謝有順表示,這些“活生生、毛絨絨”的經驗,是文學寫作的血肉基礎,遠非一些藝術修辭、藝術技巧可以替代,“我們眼中那些蒼白無力的寫作,都可以從業余寫作者中的作品里獲得啟示。”
有評論認為,業余寫作者的文字書寫,已與當代中國社會生活建立了一種對應性同構關系,通過“新大眾文藝”的生產與傳播,演變為現代化進程的一種隱喻。
“業余寫作在這個時代具有特殊意義。”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李敬澤指出,在高度流動的、復雜的社會中,業余寫作有助于打破人們僅以職業身份發生關系的局限,促進人與人之間相互打開、交流,實現相互認識和聯結。
用文藝賦能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不僅如此,發軔于東莞的“中國作家第一村”、橋頭文學模式、長安文學現象及其他文學群落,也正愈發受到文學圈內外的重視。

“中國作家第一村”
“這些寫作是‘新大眾文藝’現象的有機組成部分,人民群眾進行文藝創作的愿望和機會得到前所未有的釋放,真正形成了人民書寫、書寫人民和人民接受、人民評價、人民傳播的文藝景觀。”東莞市文聯黨組書記、主席張彤飚表示。
從打工文學的興起到作家簽約制度的建立,從“作家村”的自發形成到政府因勢利導,打造出實體版的“中國作家第一村”,從具有現象級傳播影響力的寫作群落的出現,到如今業余寫作者的集中涌現……東莞這座城市,多年來一直是文學創作的沃土。
近年來,隨著網絡平臺、社交媒體等新興媒介的興起,業余寫作者擁有了更加廣闊的展示空間。為了發掘新文藝群體、發展“新大眾文藝”,東莞市文聯做了大量工作,如出臺《東莞市推進文藝精品創作生產機制》,聯合花城出版社實施“全鏈條”培育項目,舉辦各類寫作培訓活動,搭建文學交流平臺等,實實在在為業余寫作者提供全方位支持。
據悉,圍繞“中國作家第一村”與“新大眾文藝”熱潮,東莞將重點打造成集創作研討、版權交易、影視改編、文旅融合發展等為一體的文學聚集示范地,激活文學IP轉化動能,整合資源推進“揭榜掛帥”項目,實施“文藝群落倍增計劃”,構建“主村引領、多點開花”的全域文藝生態,推動文學惠民、文化產業與鄉村振興雙向賦能,力爭打造“新大眾文藝”賦能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生動案例。
李敬澤也表示,中國作協高度重視來自基層的寫作者,各級作協要以各種方式向他們提供支持,熱心幫助他們不斷成長。
另據花城出版社社長、《花城》雜志主編張懿介紹,對于王瑛這樣的業余寫作者,花城出版社高度重視,將盡快出版王瑛的作品,同時還將從“灣區·新大眾文藝”的角度切入,通過發表出版、推介傳播、評論研討等方式,發掘更多優秀的作家作品。
謝有順期待,業余寫作者寫出更多的好作品、大作品,從而帶動更多的作家,通過東莞來認識中國、書寫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