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余 叢 | 吾心安處是故鄉
更新時間:2024-09-05 作者:余 叢來源:廣東作家網
在遙遠的鄂西大山里,有一座不起眼的村莊叫鮑坪。雖然我從沒有去過鮑坪,但是我仍然通過朋友譚功才的文字想象過鮑坪,乃至認識了鮑坪,這里既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成長的故土。直到有一天,不安于現狀的譚功才,為了謀生和發展,遠離了他的家鄉,來到遙遠的南方沿海城市,并在異鄉成家立業。正是基于這一背景,譚功才用三十年的時間,矢志不渝地為鮑坪樹碑立傳,寫出了兩部重要的散文作品集,一部叫《鮑坪》,另一部叫《鮑坪記》。從走出家園鮑坪,到回到書本上的“鮑坪”,或許功才作為作家的要義,就是為了完成某種著述的使命,現在也該放松一口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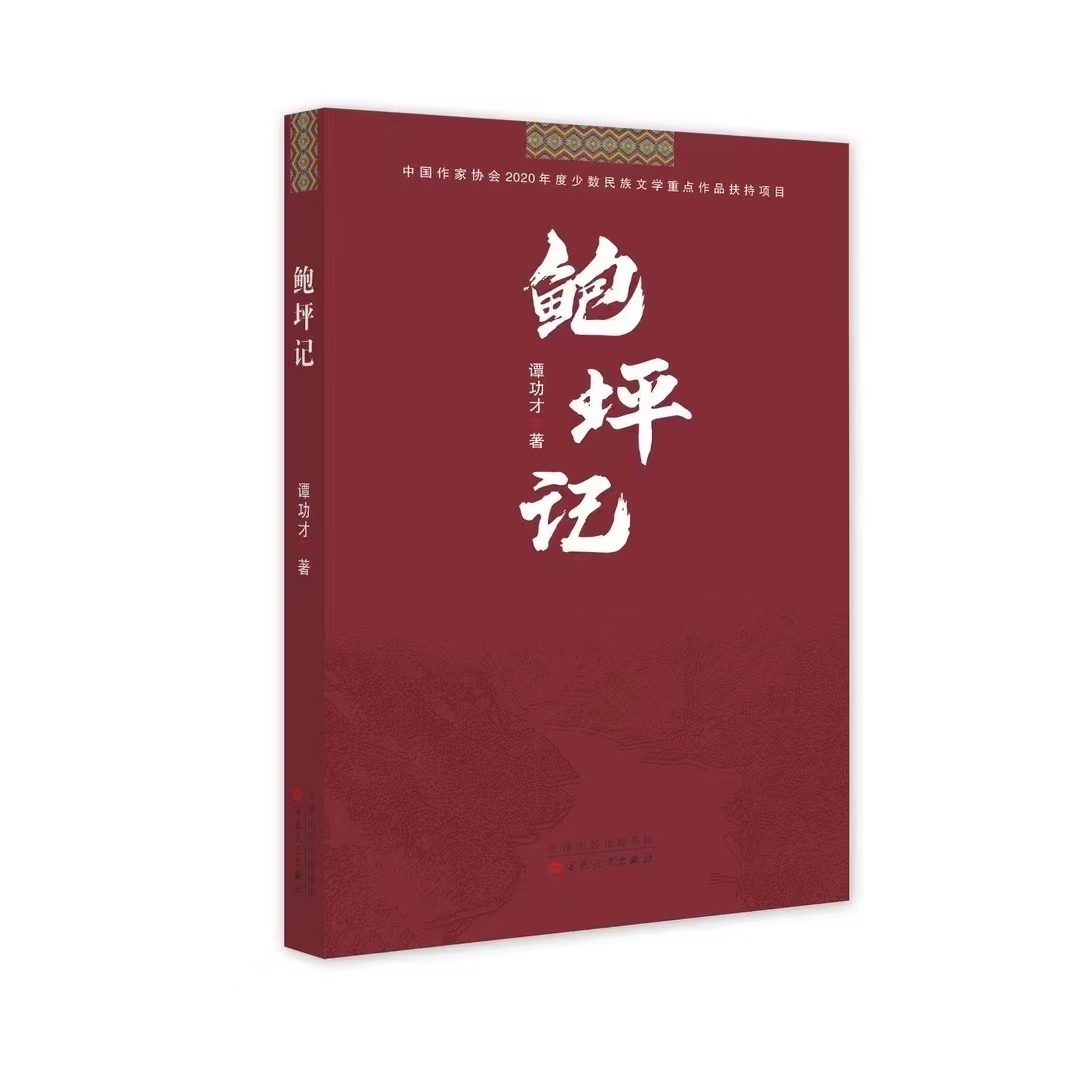
對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這輩人,大多數人的成長經歷,或多或少會有一段鄉村印跡,因此,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不盡相同的“鮑坪”。只不過譚功才把它誠懇地記錄下來,而我們卻逐漸將自己的村莊從記憶中抹去,沒有了祖輩的鄉村也只能隨之消逝。如今,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瘋狂吞噬,更多的鄉村必將淪陷于時代的推土機。顯然,譚功才的書寫是彌足珍貴的,不管是對故鄉風物的遐想與詠嘆,還是山居人情的思念與追懷,他無形中寫出了一代人的鄉愁。然而,這樣的鄉愁又能有幾分美好可言?功才筆下娓娓道來的“鮑坪”景象,處處飽含人世的辛酸和苦難,又彌漫著蹉跎歲月的感傷和悲情。而今,能夠共情的同代人已經日漸衰老,被連根拔起的后輩也只能面帶驚訝的神情,又如何能理解或審視“鮑坪記”里的生存困境。
有個譬喻很形象,藝術是患病的貝殼生出的珍珠,而鄉愁好比游子的懷鄉病。在世俗意義上,故鄉是回不去的他鄉,只有遠離了才擁有美好的印象和記憶,走近了卻又生出膽怯之心。白居易說,“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也許途中方是游子的心安之地,異鄉才是漂泊者落腳的處所,而故土只是被反復回望的風景,因此,“鄉愁”對譚功才而言不是浪漫的意境,也非一勞永逸的治愈,而是遣懷療傷的一劑藥方:再“巴掌大”的地方也有一方天地,再閉塞的山窩也有一條出路,再古老的村落也有無數盼頭。正如他所言:“只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距離,才使得我能夠在另一種文化背景的燭照下,重新審視和回望鄉土意義上的鮑坪,使之變成一種精神上的永恒。”
從《鮑坪》到《鮑坪記》,后者是前者的續篇,是譚功才對故土的意猶未盡。它們一脈相承,又互為映照,一事一物取材于作家過往的鄉村生活,一情一景受益于滋養他的那方水土。然而,字里行間隱現的愧疚、無奈和真情,乃至鮑坪人的血與淚,不正是中國山村社會的縮影嗎?假以時日,《鮑坪》二書的價值會越發凸顯,將是一部描寫鄂西山村風土人情的重要著作,或人文風物,或地理風情,或世事倫常,堪比“鄉村志”式的百科全書。當然,這得歸功于功才的散文與他的為人一樣誠懇,不炫弄不花哨,不做作不張揚。既有切身體驗,又有客觀語境,讀起來平白生動,親切感人,更有一種詩性的沉思。這樣本真而清峻的散文,恰恰在當下喧囂的文學現場顯得稀有,同時,作家通過文字對原產地鮑坪的重新定義,構建了自我心靈上的歸宿。
人生如云駐,故土亦不過是生命的驛站。《鮑坪》和《鮑坪記》二書,宛如譚功才的一曲哀嘆的“呼愁”,也將是我們朋友的眼中,鄉村文明的最后挽歌。隨著城愁時代的來臨,精神上的返鄉和尋根,變得更加迷茫和無法辨識,而數字化的未來,必然定義虛擬空間的“鄉愁”。然而,每一種“鄉愁”都是深情的遺憾,在被思維和算法駕馭的非物世界,“鄉愁”也將被數據肢解為碎片化的情態。總之,每個人都身處歷史的大潮,被洪流裹挾或淹沒,只有強者捆綁著石頭浮出水面。當數字化秩序接替了大地的秩序,即使來自鮑坪的譚功才,終歸無法逃脫蘇東坡那句至理箴言:此心安處是吾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