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黃燈 | 走進學生家,讓我有機會預設親人的另一種生存
更新時間:2024-03-11 作者:周欣怡來源:羊城晚報?羊城派
2020年,二本院校教師黃燈所著的《我的二本學生》引發(fā)社會對“二本學生”這樣一個數量龐大而又被忽視的群體的關注,以及對大學教育的討論。
四年后,黃燈的新作《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2》出版。這部集結她五年漫長家訪旅程的作品,記錄下她在云南、湖北、安徽、廣東等各地村莊、小鎮(zhèn)、山坡、街巷的足跡。
五年來,她乘坐高鐵、動車、長途客車、摩托車,從城市向散落在山海之間的鄉(xiāng)村走去。這種貼近大地、回到起點的走訪,讓黃燈獲得了講臺之外的更多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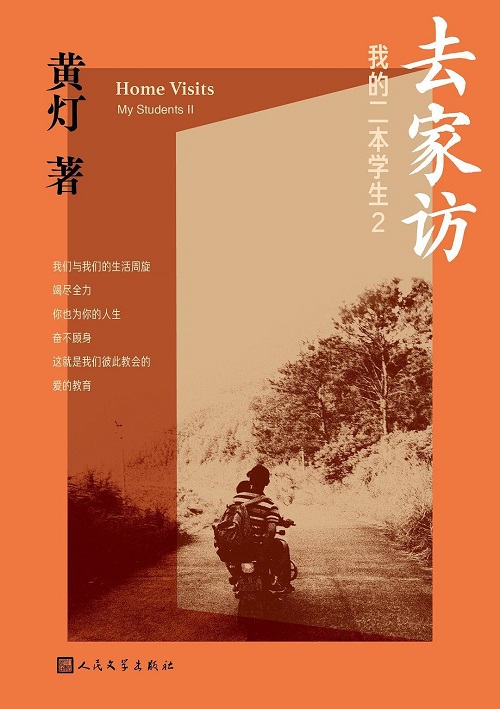
而通過傾聽,在感知不同地域、不同家庭相同氣息的同時,黃燈也在一次次行走中,喚醒了自己對故鄉(xiāng)、對工廠、對祖輩、對親人的記憶。感受到教師這一職業(yè)的莊重和尊嚴,感受到教育的柔軟、美好和力量。
她在序言中提及家訪為自己帶來的饋贈:“和年輕人站在一起,直面真實的社會、自主抵擋生命的慣性消耗、盡可能和更多的人建立關聯(lián),并在具體的生存細節(jié)和生命場景中,以下蹲的姿態(tài),激活各自的生命活力,積蓄可持續(xù)的起跳能量和力氣。”

黃燈與學生及其家人的合影
是什么驅動力讓黃燈老師這樣堅持?面對年輕人的迷茫,面對教育體制現存的一些問題,作為教師還能做些什么?近日,羊城晚報記者專訪了黃燈——
“到現場去”的寫作
羊城晚報:去家訪學生的初衷是什么?
黃燈:學生是我最想寫作的對象群體。在原來的設想中,《我的二本學生》就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基于講臺視角的從教經歷與觀察,其二就是走向講臺背后對學生家庭的尋訪與觀察。《去家訪》這本書算是對第二部分內容的呈現。
我在2018年開始寫《我的二本學生》,但在2017年就已經開始了漫長的家訪旅程。站在講臺上只能看到學生的一個層面,我想更多地去了解他們,就需要看到他們家庭的層面。所以,去學生家里看看是我多年以來的心愿,但真正落實是從2017年暑假開始的。
羊城晚報:什么時候決定把家訪經歷書寫下來?
黃燈:在寫《我的二本學生》的時候,本來準備把家訪也寫進去,但后來發(fā)現講臺視角的部分寫完后,內容已經能夠自成一體了,若把家訪部分硬摻進去,結構不太協(xié)調。于是就有再寫一本家訪的想法。
羊城晚報:《我的二本學生》出版并引起關注,這對您關于家訪的寫作產生什么影響?
黃燈:原有的寫作計劃沒有改變。家訪是集中對我教學行為的敘述,我看到什么就寫什么,視角相對有限。但《我的二本學生》出版了以后,確實引起較多關注,我得以和一些教育學者有過交流,也參加過相關的教育學術會議,還收到了很多年輕人反饋的感想。
這些促使我對教育產生一些新的思考。比如,關于原生家庭對孩子的影響,是否真像輿論宣傳的那么確鑿?我觀察發(fā)現,原生家庭對年輕人的影響是有的,但并不絕對,其中有很多能動性。挖掘這方面的信息很重要,也能讓學生覺得有力量,生活有奔頭。
另外,在和一些教育學者討論后,也有很深的感觸。我不太了解教育學理論,我所做的就是我自己的教育實踐,我對教育的觀察都來自于我對學生的觀察、對我自己成長經驗的喚醒,包括父母對我的教育、我對我的孩子的教育觀察等維度。這些完全都來源于個人的生活經驗。
和一些學者接觸以后,發(fā)現他們的研究路徑是不一樣的。在他們看來,我是在做教育學的質性研究,而站在我的角度,其實就是在做非虛構寫作。
這些碰撞讓我的思路更開闊,有時甚至會突然“喚醒”我。例如,現在的我會下意識地在教學中滲透一些教育實踐。上寫作課時,不僅教學生怎么寫,還會觀察他們學完這門課程后有些什么變化。所以《我的二本學生》的出版,讓我感受到教育不是懸在空中的,它是一門科學,很實在,看得見摸得著,可以通過具體的課程來實踐。
羊城晚報:《去家訪》一書涉及大量的信息資料,具體是怎樣寫成的?
黃燈:我做家訪的節(jié)奏并不快,每年只去幾戶人家,一去都會待上幾天,跟學生的父母交流,學生也會帶著我去看他們以前生活過的地方,是一種深度的走訪。這持續(xù)了5年。當時會拍些照片,記下要點、關鍵詞,重要的訪談也會錄音。正因為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寫的時候就能回到當時的狀態(tài)。
但《去家訪》是我寫得最難的一本書。5年的家訪內容,不算上整理材料的時間,僅初稿寫作我就集中用了八九個月時間。那時候是疫情期間,時間稍微多一些,我就像寫博士論文一樣,把自己關進圖書館。那些龐雜的錄音材料和記錄都需要重新梳理,相當于我再重新走了一遍家訪旅程,將其在文字上重現。
我能感知到那些細節(jié),當時我的處境、心理狀態(tài),都是刻骨銘心的。所以,我認為一定要到現場去,去和不去的收獲肯定不同,不去是不踏實的。
寫二本學生是自然而然的事
羊城晚報:除了寫法上的,家訪過程中有什么困難?
黃燈:我寫作的核心都是在理解學生的成長,敘述他們的成長,所以寫作的難度也主要表現在這方面,要去理解不同的學生,他們的成長處境千差萬別。其他倒沒什么困難,無非就是買張票,和學生家長溝通好。整個家訪過程在心理上是很舒適的,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事,而且很享受這個過程。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家訪的重要性在哪里?
黃燈:在大多數家庭里,孩子跟父母平時很難一本正經地去聊一些事情,但如果有外在力量的介入,可以達成一個聊天的氛圍,說些平時沒有契機傾訴的話。在家長、學生和我三者都在場的時候,交流的氛圍都很好。
有的孩子可能在過去對父母會有一些誤解,在我去家訪以后,他們其實有了一個重新認識對方的契機,因為家訪這一行為帶來了一種融合,像催化劑一樣,促進他們之間的交流溝通和理解認識。
羊城晚報:家訪要花費很多時間,這不得不犧牲自己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黃燈:這幾年的寒暑假我主要都在做家訪,稍遠一點的地方只有假期才能去。我兒子曾經抱怨說,從沒帶他出去旅游過,對比別的家庭,哪怕放三天假都會有旅行規(guī)劃。在他小時候,我確實因為太忙較少帶他出去玩,他后來也表示能夠理解。
但是我很看重對兒子的陪伴。只要有機會,基本上每周都會堅持和他進行一次深度聊天,兩個人認真且沉浸式地進行對話。他愿意和我講很多心里話。同時我很支持他的興趣愛好,盡可能地滿足他所熱愛的事情。比如他喜歡汽車,我會抽時間帶他一起去看車展,他想開卡丁車,哪怕在高中期間,只要有空,我也會帶他去。他會覺得媽媽是理解他、支持他的。
羊城晚報:這么多年來您堅持非虛構寫作,是否出于一種責任感、使命感?
黃燈:我不覺得非虛構寫作有多高大上。但是做這件事情很重要,就像二本學生這一重要群體居然沒人關注,我會很奇怪。從開始教學起,我就很關心學生的生活狀態(tài),也非常感興趣,這些年學生給我寫的短信、發(fā)來的郵件、他們的作業(yè)、試卷我都保留了下來,積累多了就會有感覺,覺得應該有個人發(fā)起一個話題來集中討論這個群體。當然寫一個作品出來就是最好的話題,所以寫二本學生是自然而然的。
羊城晚報:在寫作中您對自己有怎樣的要求?
黃燈:非虛構寫作在很多方面與深度調查有些相通,都傾向于對真相的探尋的。在任何一個年代,老百姓都會對真相感興趣。
我對寫作的要求非常嚴格:材料掌握到什么程度,他們關于一件事談到什么程度,我就寫到什么程度,不加任何編造,如實地呈現。書中哪怕是一條公路都是很清晰的,為了讓地理方位更準確,我會打開地圖仔細對照,看看我們經過了哪條路。可以說按照我書中的指引就能去到學生家里。
其實這個寫法很累。打個不恰當的比喻,非虛構寫作就是用文字拍紀錄片,速度快不起來,因為每一句話都要落到實處。我在2003年寫過20多萬字的隨筆,只花了20多天在房間里就寫完了。我感受過寫作的速度,那時候寫得快因為是對我個人經驗的一種表達,而我寫非虛構就會覺得進度很慢。
老師對學生應該是有愛的
羊城晚報:您很容易和學生打成一片,成為他們信任的人。如何做到這點?
黃燈:我跟學生之間沒什么距離,學生在我面前很自在,很多人說我就像他們的家人一樣,沒有隔閡。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我很簡單直率,待人也真誠,不說假話。現在大學生的困惑也很多,有個傾聽者很重要。他們可能對于我這種性格特質的人容易產生訴說的意愿。
羊城晚報:對于學生傾訴的困難,老師應該如何引導?
黃燈:其實老師能做的很有限,有時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他們需要精神力量,需要有人看見他們、懂他們的心思,能夠疏導、指引他們看到別的角度。比如有的學生不知道如何規(guī)劃學業(yè),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歡什么,這個時候老師就能提供一些具體的建議。
還有些學生向我傾訴困難,可能與學業(yè)無關,我也會先聽他們訴說,結合我自己的成長經歷,盡可能引導他們坦然去面對。既然學生找到我傾訴,作為老師,就算不能給到實際的幫助,也可以提供精神和心理支撐,老師對學生應該是有愛的,能讓學生感受到“老師是理解我的”。
羊城晚報:您對學生的挖掘和書寫是否也是在回顧自己,書寫自己?
黃燈:我在寫作的時候有一些代入感。我對二本學生算是觀察得比較深,也是因為我和他們其實是一樣的。一方面我看到學生的成長,另一方面我看到自己的成長。
我在寫《大地上的親人》的時候,會想到書中那些人群,我的外甥、侄子、堂弟,那些80后、90后,如果沒有遭遇留守兒童或者外出打工的經歷,如果他們考上了大學會有怎樣的命運。其實《我的二本學生》系列就回答了這些疑問。我所教的學生年齡跨度囊括了上述各個年齡段的親人。
老師這一職業(yè)讓我擁有機會預設親人的另一種面向、另一種生存。而我的學生家長基本算是我的同齡人,家訪讓我獲得了和他們直接交流的機會,我對他們又有了進一步觀察和理解。
每次走進學生家,我都懷有特別的期待和真實的雀躍,見到家長的那一刻,內心充盈著一種久違的溫情。這種讓人放松、沒有隔膜、彼此敞開的關系,固然來自師生之間的信任,更來自我和我的同齡人——學生家長之間,因為共同的時代記憶所產生的共鳴,在以家訪名義的遙遠回望中,不需要語言,我們就能跨越具體的現實處境,滋生出一種別樣的理解和默契,感知到彼此的心心相通。
羊城晚報:老師的科研壓力、生存壓力及家庭壓力,和他們教書育人、關心關愛學生,這些要怎么平衡?
黃燈:其實對我來說,授課、寫論文、做課題沒有太大難度。我在2014年已經評上了教授,我現在的寫作對科研成果或是職稱評定沒有任何影響,純粹是出于喜歡才去做的。
但是剛入職的年輕教師很難有這種精力,所以不能要求每個年輕老師像我這樣去家訪,這完全看個人選擇。客觀說來,現在年輕老師的壓力比我們讀大學時老師的壓力大很多。
有學校領導問我怎樣調動老師的積極性,我就說:“學校對老師好,老師就會對學生好。”學校給老師盡可能地減負,減少一些事務性工作消耗他們的精力和時間,他們就會有時間和精力去管學生。老師天然是愿意帶學生的,這是教師這一職業(yè)成就感的一個很重要的來源。學生不是老師的麻煩,而是老師的幫手,也是讓老師成長的動力源。所謂教學相長就是如此。
成就來源于熱愛和激情
羊城晚報:如今老師的教學科研壓力大,大學對學生科研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以及就業(yè)環(huán)境越來越“卷”,您認為一個負責任的好老師應該怎么做?
黃燈:既然身為老師,應該都會覺得年輕人的成長是個重要話題。寫論文、評職稱當然很重要,但在我的工作理念中,最重要的,是盡最大可能把學生培養(yǎng)好。學生的順利成長,找到好工作,他背后的家庭就會安定下來,這具有社會意義,對老師而言也有成就感和獲得感。
那么回到老師的生存壓力和對于學生的關心二者之間的平衡,我覺得年輕老師要做好自己的規(guī)劃,一方面不能對學校的評價體系完全置之不理,另外一方面也要去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
羊城晚報:現在網上有些教授說家境普通的學生慎選文史哲專業(yè),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黃燈: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很多人總以為大學教育是萬能的,這不一定。好多人沒讀大學,但是出于自身的喜愛,在文科方面也能做得很好。雖說這樣的畢竟是少數,但其實每個人都有他所擅長的一面,就看有沒有發(fā)現自己的特長,以及是否被破壞掉,是否堅持下來。
我見過很多這樣的學生:找不到自己的所長,什么事都能應付,也可以憑借聰明才智完成任務,但并沒有很強烈的熱愛和激情。這樣其實很容易內耗,也很難將事情做到極致。很多人覺得自己很普通很平凡,因為他們沒有找到內心的驅動力到底是什么。這就是現在學校教育的有限性。
千篇一律的應試教育標準破壞了學生對特長的發(fā)掘和堅持。一個社會人只要有一個長處就可以在社會立足,尤其在智能時代。但是現在的教育已經定好了標準,要求人不能有任何一塊短板,而且每個板子的齊整度要差不多。所以真正成才的人畢竟不多。
一件事情做到極致一定是來自熱愛和激情。我對我的學生持續(xù)地關注和記錄也是因為對人的成長始終是感興趣的,所以才會不斷地去分析它。
羊城晚報:接下來您有什么寫作計劃?打算寫小說嗎?
黃燈:暫時沒有打算寫小說,以后有些合適的題材可能會寫一些散文。當然我會持續(xù)保持對學生、對年輕人的關注,繼續(xù)走進學生家里。

原文載于2024年3月10日《羊城晚報》A8百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