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biāo)題

標(biāo)題
內(nèi)容
楊黎光:58萬字長篇小說為“深圳百姓生活史”作注
更新時(shí)間:2023-11-03 作者:戴雪晴 李培來源:南方+
日前,中國作協(xié)報(bào)告文學(xué)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楊黎光的長篇小說《尋》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近年來以報(bào)告文學(xué)寫作著稱的楊黎光,歷時(shí)4年創(chuàng)作了這部58萬字的長篇小說,為“深圳百姓生活史”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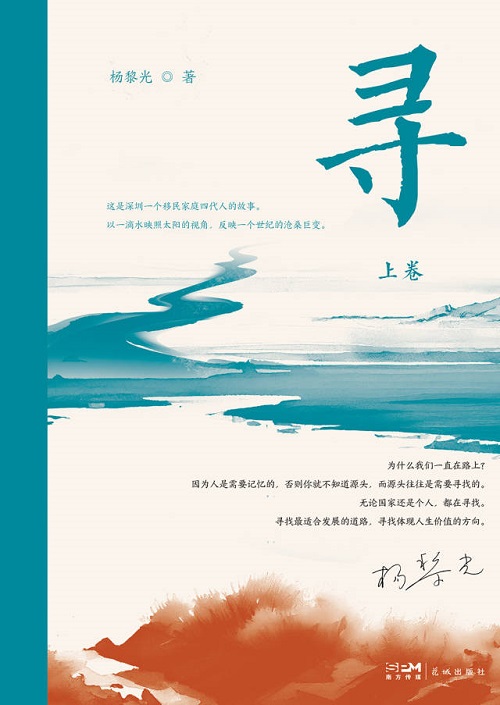
《尋》
闊別27年再度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
2019年,廣東省作家協(xié)會啟動的廣東省“改革開放再出發(fā)”作家深扎創(chuàng)作活動,楊黎光開始萌生了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念頭。在深圳生活多年的他,為這座城市創(chuàng)作一部長篇小說的愿望愈發(fā)強(qiáng)烈。他迅速提交了創(chuàng)作計(jì)劃,并成功入選。

楊黎光近照
30年來,楊黎光一直以報(bào)告文學(xué)創(chuàng)作享譽(yù)文壇,筆耕不輟記錄時(shí)代變遷。自1993年起撰寫了《沒有家園的靈魂》《瘟疫,人類的影子》《生死一線》《大國商幫》《家園》等多部報(bào)告文學(xué)作品,并三次獲得魯迅文學(xué)獎等獎項(xià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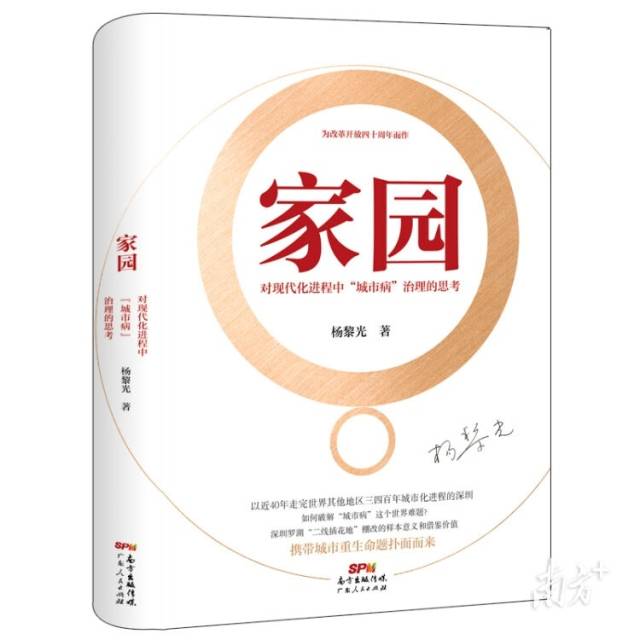
《家園》
不過,楊黎光1992年來到深圳前,便已創(chuàng)作了兩部長篇小說《走出迷津》《大混沌》。來深圳后于1996年,他又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園青坊老宅》,并入圍第七屆茅盾文學(xué)獎。時(shí)隔多年再度重拾長篇小說的寫作,在他看來,是一次難能可貴的“回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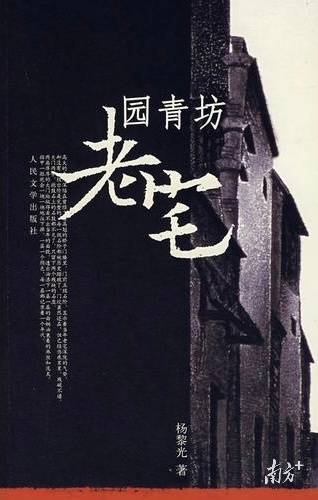
《園青坊老宅》
著力描摹大時(shí)代小人物的故事
在小說《尋》中,楊黎光撰寫了一個深圳移民家庭四代人的故事,時(shí)間從抗戰(zhàn)時(shí)期東北的白山黑水跨越到南海之濱的粵港澳大灣區(qū)。第一代老爺爺馬衛(wèi)山出生于山東,是東北抗聯(lián)的老戰(zhàn)士,第二代馬小軍出生于東北,是深圳特區(qū)的“拓荒牛”,第三代馬立、馬正出生于廣州,在深圳成長,如今是建設(shè)特區(qū)的中堅(jiān)力量,而第四代馬棽棽在美國出生,學(xué)成后毅然歸來大灣區(qū)工作。
一個世紀(jì)、一個移民家庭、四代人,縮影時(shí)代變遷。國貿(mào)大廈“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股票發(fā)行、南方談話、粵港澳大灣區(qū)建設(shè)等大事件,都與主人公的命運(yùn)起伏密切相連。“小說里的人物,都是在基層默默耕耘卻又不可或缺的時(shí)代弄潮兒,一同勾勒出這個時(shí)代最朝氣蓬勃的影像。”楊黎光說。
楊黎光坦言,小說取名“尋”,表達(dá)了他的創(chuàng)作主旨——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都在尋找最適合發(fā)展的道路,尋找體現(xiàn)人生價(jià)值的方向。
這部小說有怎樣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南方+記者專訪了楊黎光。
對話
讓中國人的“韌勁兒”延續(xù)下去
人物寫作絕不能“臉譜化”
小南:《尋》與您之前的作品相比,呈現(xiàn)出哪些變化和突破?小說名稱為什么只有一個“尋”字?
楊黎光:這一次,我從微觀視角出發(fā),寫一個深圳移民家庭四代人的故事,期許以一滴水映照太陽的視角,反映一個世紀(jì)的滄桑巨變,同時(shí)回顧了深圳四十年多來的建設(shè)歷史。
只有一個字的小說名稱的確不多見。“尋”實(shí)則有一明一暗兩種含義。明線是兒子馬小軍尋找母親的故事貫徹始終,暗線則是我最想表達(dá)的主旨——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都在尋找最適合發(fā)展的道路,尋找體現(xiàn)人生價(jià)值的方向。
小南:小說中刻畫了大歷史背景下小人物的命運(yùn),您怎么看待時(shí)代與個人的關(guān)系?怎么把人物寫活?
楊黎光:時(shí)勢造英雄,時(shí)代的變化決定了個人的命運(yùn)。國家走上正確的發(fā)展道路時(shí),機(jī)遇就會增多,人們的生活會變得更好,城市也是如此。
不管時(shí)代車輪如何向前,人們還是有其堅(jiān)守的品德,例如小說中的家庭就有個傳統(tǒng)——不管家境如何,吃飯時(shí)絕不能掉下一顆米。
我在《尋》一書中塑造了很多人物。在構(gòu)思整部作品時(shí),人物的基本定位要確定,不然小說立意很難成立。同時(shí),我要反復(fù)提醒自己,不能使人物“臉譜化”,而要努力使人物形象立體飽滿,為此我采訪了很多人。
小南:在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有沒有特別的經(jīng)歷和感受?
楊黎光:小說創(chuàng)作前我看了很多史料,包括東北抗聯(lián)的歷史,把自己要塑造的人物時(shí)代背景弄清楚,了解一個世紀(jì)以來中國人在極其困苦的情況下,對改變命運(yùn)的那股韌勁。這種韌性是極為寶貴的,又一代一代地承續(xù)下去。這種精神也鼓舞了我的創(chuàng)作。
上世紀(jì)80年代初,為了深圳特區(qū)的建設(shè),兩萬基建工程兵轉(zhuǎn)業(yè)到這里。他們是深圳的第一批“移民”,也是深圳最早的“拓荒牛”,這段歷史不應(yīng)被忘記,作家有把他們記錄下來的責(zé)任。
作家要跳出自我認(rèn)知框架
小南:這次為何選擇用小說來講述深圳百姓的故事?
楊黎光:我是1992年1月到深圳的,熱火朝天的時(shí)代氛圍深深感染了我,從1993年起,我撰寫了大量的報(bào)告文學(xué),而我在深圳幾十年來又從事的是記者工作,因此,我既是深圳發(fā)展的記錄者,也是參與者。多年來,我一直想為深圳寫一部長篇小說。雖然大多數(shù)讀者都認(rèn)為我是報(bào)告文學(xué)作家,但其實(shí)我最早是寫小說出身的,因此,《尋》的創(chuàng)作對我來說,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回歸”。
小南:報(bào)告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小說創(chuàng)作對您來說有何區(qū)別?
楊黎光:報(bào)告文學(xué)是紀(jì)實(shí)的藝術(shù),我所寫的大部分報(bào)告文學(xué),是從宏觀角度來反映歷史的。小說則是虛構(gòu)的藝術(shù),從微觀角度來表現(xiàn)蕓蕓眾生。
雖然小說是虛構(gòu)的,但它所反映的生活必須是真實(shí)的,它要讓讀者相信,生活中真的會發(fā)生這樣的故事,即你的構(gòu)思深扎在生活的泥土中,這種信念感對于作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體會,小說的創(chuàng)作與報(bào)告文學(xué)最大的不同是語言,我很久沒有寫長篇小說了,這回要轉(zhuǎn)化為小說的語言,對我來說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小南:在您看來,當(dāng)代作家為何應(yīng)該扎根生活?
楊黎光:自2019年起,我便開始到深圳天健集團(tuán)體驗(yàn)生活,這個集團(tuán)的前身是基建工程兵302團(tuán)。通過這次“深扎生活”,基建工程兵的故事給了我許多靈感。后來,這些故事對我構(gòu)思情節(jié)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我看來,有一種作家只能寫自己生活的領(lǐng)域,這種寫法往往容易陷入自我認(rèn)知的框架內(nèi),對廣闊生活背景的把握不夠。如果能深深扎根在生活中,接觸不同的領(lǐng)域,更可擁有廣闊的視野,寫出好作品。文學(xué)源于生活,這句話有很深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