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鄧一光、魏微、葛亮集體北上亮相,“文學粵軍”尋求突破
更新時間:2023-03-07 作者:劉長欣 郭珊 來源:南方+
2月24日,中國現代文學館。在《人,或所有的士兵》研討會開始之前,岳雯、李蔚超、李壯等評論家頗具儀式感地走到一起,排隊向該書作者、廣東作家鄧一光致敬。這一幕,讓在場的廣東省作家協會創研部主任周西籬心中一顫:“這凸顯了作品征服人心的價值力量。”
除了鄧一光,一同在京召開研討會的廣東作家還有魏微、葛亮。作為“文學粵軍”的中流砥柱,他們此次集體北上,用作品向全國文學界展現了廣東文學創作上的轉型與升華。
以“戰爭文學譜系”蜚聲文壇的鄧一光,這次將目光投向了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身為廣東文學院院長的魏微,在新作《煙霞里》中通過對“70后”女性田莊40年命運的書寫,實現了對三代人成長的編年;深受江南書香浸潤的葛亮,與其筆下《燕食記》的人物一起探尋嶺南味覺演化史,完成了其人其文與灣區文化的深度融合??盡管類型、題材不同,這些作品都是灣區故事、中國故事的精彩濃縮,也是跨地域遷徙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結晶,為新時代廣東文學、中國文學帶來了更豐富、更遼闊的可能性。
正如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鄧凱所言:“今天的廣東文學處在一個繼往開來、再創輝煌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廣東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張培忠更是信心滿滿:“我們對新時代廣東的真正書寫才剛開始。”
01、題材
“講好嶺南故事、講好中國故事”
“每個文學創作者都被賦予了新的時代要求,而嶺南的人文質地中天然的現代性恰恰與傳統文化之間構成了美妙的對位,講好粵港故事、嶺南故事,也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前提。”作家葛亮在研討會上這樣講述自己對當下長篇小說創作的思考。
生長于江南,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葛亮坦言,他一直能感受到自己身上“江南和嶺南之間的文化流淌”。而“吃”作為嶺南文化最為知名的招牌之一,更是令他念念不忘。

葛亮一直深信,如張光直先生所說,想要親近一種文化,最好的法子莫過于通過它的“胃”,經過味蕾的賦予,打開文化的“窺口”。
葛亮曾在《北鳶》里寫安徽毛豆腐、益陽松花蛋,由此剖析中國人對待傳統與變革的態度。這次在《燕食記》里,他又將“常與變”的辯證與博弈,放到四代粵點師傅的傳奇身世及薪火存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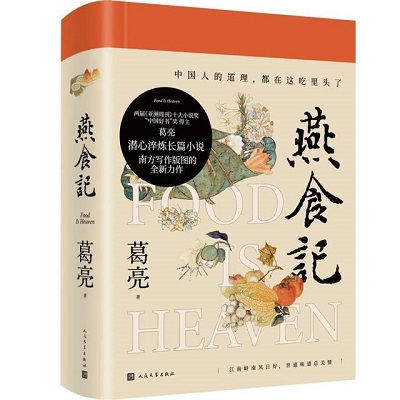
研討會上嘉賓們津津樂道的,少不了《燕食記》中提到諸多南粵名菜、名點。其中有一道“禮云子”(蟛蜞籽),名字出自《論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最樸素的食材里竟也蘊含著深沉的君子之道。
“難以想象,像這樣一個江南的男子,竟然能如此‘吃透’嶺南。”中國作家協會創作聯絡部主任彭學明感嘆,“嶺南的文化血脈水乳交融地呈現在葛亮的文字骨血里。”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更是將《燕食記》稱作是“嶺南夢華錄”。
原籍江蘇的魏微,同樣是以“遷徙者”的視角,審視自身的灣區生活痕跡。她曾經輾轉北京、南京等多個城市,2005年成為廣東省專業作家。在廣州生活多年,她以廣州為題材的寫作卻并不多,她始終覺得:“離得太近了,反而寫不好。”
沉淀十多年后,她終于捕捉到最契合心靈的敘事方式。在《煙霞里》,她借主人公40年命運軌跡,以別具創意的“編年體”,囊括鄉鎮、縣城和一線城市等多種生活體驗,包括南下廣州、個體經濟、買房炒股、舊城改造、招商引資、互聯網興起等。“我是貼著自己來寫田莊這個人物的。”她這樣說。
原籍湖北的鄧一光,于2009年遷居深圳。“山海之城”,是他對深圳這座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南國都市最初的印象。他眼中,這座城市氣候宜人、植被豐茂,新鮮觀念層出不窮,充滿澎湃的活力和無限的可能性。他因此萌生出一個被文學評論界稱為“現象級”的城市寫作計劃——創作“深圳系列”中短篇小說100篇,目前已完成過半。
或許是受到深圳“地氣”影響,年近七旬的他仍樂于自我革新。在新書《人,或所有的士兵》,他將目光聚焦到太平洋戰爭背景下的香港保衛戰,以繁復獨到的結構、冷靜深刻的文字,完成了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對戰俘營的首次正面書寫。
“縱觀歷史,從來沒有哪一個時代給文學提供了如此宏闊、如此深刻的人生實踐和生命體驗。”張培忠稱,“采九州之精華,納四海之新風”,粵港澳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創新性,為今日廣東作家、灣區作家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豐沛的資源。
02、探索
“舍得下功夫”,文學才有“活氣”
著文如烹飪,筆耕跋涉、苦心醞釀,都是出于對食材的“敬重”之心。創作歷程的艱辛,有評論家借用《燕食記》里的名粥“融金煮玉”來類比——除了水好、米好,有“活氣”的秘密,無非是“舍得下功夫”。
身為原作者的葛亮,顯然對此深有體會。為了保證寫作的嚴謹,他用了6年時間,做了大量案頭工作,并走訪了廣東、香港多地進行田野調查,考察粵菜食源開發、食具制作、食品烹制等諸多細節。在寫到頭茬“霧水荔枝”時,從荔枝的種類、特性、吃法,他都作了詳盡的考證和辨析。
作家的“中年危機”,這是魏微近年來經常提到的一個詞。她坦言,寫作的內在驅動力不像年輕時那么明顯了,“有時心力跟不上,有時筆力跟不上”。然而,《煙霞里》之于魏微,就像《呼蘭河傳》之于蕭紅,一生只為這一本,她必須傾力而為。

《煙霞里》主人公田莊的生命歷程背后,是近半個世紀中國社會的巨變。為此,魏微對中國當代社會經濟史,進行了非常詳實的調查研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閻晶明將此形容為“作家編年譜”,來不得半點虛假。
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委員會副主任潘凱雄留意到,《人,或所有的士兵》所引文獻資料有45條,據他估計,所涉參考文字“起碼達到上千萬字”,而鄧一光大概記得“讀了70多本書”。這股“像寫學術著作一樣創作小說”的嚴肅、自律勁頭,令潘凱雄甚為嘆服。
既扎實縝密,又勇于自我挑戰,三位作家的共同創作特性,某種意義上也成為對嶺南文化務實、進取的印證和呼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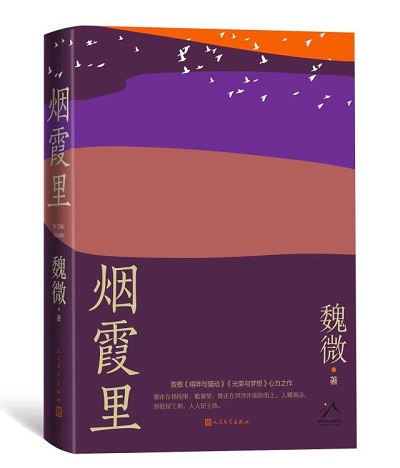
魏微此前的作品以細膩婉轉的抒情特質見長,而《煙霞里》則要求作家對宏大歷史構建,要有一種“豁出去”的“力量感”。作家李洱敏銳指出魏微創作上的變化:“《煙霞里》對時代脈搏的把握,對個人命運和大時代之間那種細小、直接的關系的建立,下手非常準確,利落,堅實。”不僅如此,魏微還將紀傳體、編年史、田野調查、散文筆法等熔鑄一爐,創造了一種嶄新的小說文本。

《人,或所有的士兵》具有拼圖似的復雜結構和多聲部敘述特色,書中關于不同國家、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的描寫,特別是語言的鮮活運用,讓讀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按長篇小說選刊主編宋嵩所說,這部作品“將‘聲口’表現得淋漓盡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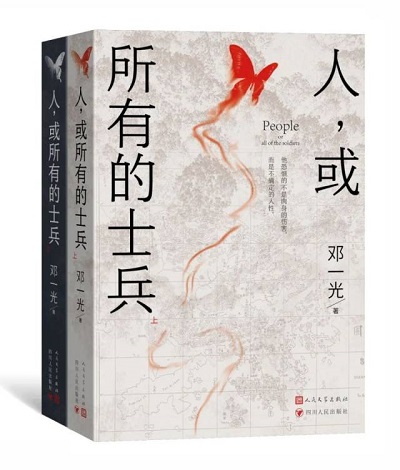
書中的東江縱隊使用兩種語言,一是客家話,二是軍隊內部使用的“軍話”,鄧一光都特意進行了鉆研。而他精通日語的兒子,全程擔綱日語指導老師。鄧一光說:“語言、語氣的準確表達,是作品讓讀者信服的關鍵。”
無獨有偶,葛亮在新書中也經歷了語言上的冒險。他嘗試把粵語中生動的口語化表達和古雅的漢語結合在一起,寫出一種亦古亦今、類似粵菜“既精致又清淡的味道”。
03、展望
夯實創作根基,推動“文學粵軍”出海
在三位作家集體北上、在京掀起文學旋風的背后,是更多的廣東作家在文學世界里開拓奮進,試著觸達更為廣闊的疆域。
在去年揭曉的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上,深圳作家蔡東憑借《月光下》獲得“短篇小說獎”。作品嘗試表達一種嶄新的都市觀和人文觀,讓“古老的詩意轉化為現代經驗的內在光亮”。陳啟文創作的首部全景式展現東深供水工程建設者事跡的長篇報告文學《血脈——東深供水工程建設實錄》,榮膺廣東省第十二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此外,王威廉的“純文學科幻”系列,吳君的港深“雙城記”——長篇小說《萬福》,阿菩的《十三行》系列,林棹的魔幻現實風格新作《潮汐圖》等作品都引起了文學評論界的廣泛關注。
事實上,“文學粵軍”還將拓展的目光投向了更遠的地方。
據悉,《煙霞里》《燕食記》《金墟》等廣東文學作品入選了首批“揚帆計劃·中國文學海外譯介”推介作品,這將是這些作品“出海”的第一步。在此之前,2022年12月,熊育群、王威廉、鄧一光、王十月等十余位廣東作家,出席匈牙利讀者俱樂部的交流活動,通過獨具地域特色、時代風貌的廣東文學,展示當代中國生機蓬勃的社會現狀。
在未來,大灣區作家如何進一步集體發聲,提升“文學粵軍”的影響力?中國作協外聯部主任張洪斌建議,可考慮通過“一帶一路”文學聯盟、中國海外讀者俱樂部等平臺和機制,推介廣東文學作品。張洪斌表示:“廣東作家講的很多故事,對于海外讀者來說,有著很獨特的吸引力。”
若想要高聳的“塔尖”,離不開深廣的“塔基”。在夯實廣東文學根基這個問題上,廣東省作協給出的答案是:以深入生活鍛造精品力作,培育人才梯隊。
記者獲悉,今年2月,廣東省作協連續第4年被中國作協評為年度“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題實踐先進集體。接下來,省作協將積極落實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組織創作“新版《人世間》”,充分挖掘群眾創新創業、誠實守信、勤勞致富的故事,打造一批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扛鼎之作。
另一方面,廣東省首個中國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時代文學實踐點落戶深圳前海。該實踐點將組織作家采訪采風、開展文學志愿服務、提供“深扎”體驗等,為濃墨重彩講好中國故事、灣區故事提供契機和平臺。
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邱華棟在實踐點啟動儀式上熱情呼吁:“希望新時代文學實踐點成為當地作家的一塊文學根據地,作家們在這塊根據地上深入開掘、充分表現,創作出屬于新時代的新史詩!”
張培忠表示,對于廣東作家、灣區作家來說,“對新時代廣東的真正書寫才剛開始,我們對未來廣東的創作充滿信心。期待經過歲月的洗禮,能有更多廣東文學力作,成為灣區的文化名片、中國的文化名片。”
●專家點評
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副主任潘凱雄:
三位作家實現了自我突破
魏微、葛亮、鄧一光等三位廣東作家此次帶來的新作,都實現了一種自我突破。
《煙霞里》的基本特點是“三個兩”,分別是兩個編年史、兩種文體置、兩個敘事主體,這三個“兩”涉及到長篇小說創作上兩個最基本的問題,即結構問題和敘事問題。《煙霞里》在這兩個最核心的要素上把握住了。這部作品,對魏微來說有質的飛躍,她的格局變大了。
《燕食記》是一部特色鮮明、極有特點的作品,且藝術編織得非常周密,文字十分講究,內容特別厚實。從《朱雀》《北鳶》到《燕食記》,“中國三部曲”呈現出不同的樣式、形態,一部比一部好。這些創作過程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一種可貴的成就——葛亮始終處在上行軌道上。
鄧一光是中國當代最會寫戰爭、最會寫軍人的作家之一。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他把中國抗戰納入到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體系當中書寫,也是我們的文學走向國際化、全球化歷程當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作品的主人公,從鄧一光過去筆下的“戰神”變成現在的戰俘,體現了以人為本、生命至上的觀念。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鄧凱:
廣東文學歷來都是探索者和弄潮兒
兩千年來,嶺南文化為廣東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近代,廣東更是得風氣之先,以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學風格,成就代表中國文學發展流派之一的嶺南文學。
從黃遵憲、梁啟超倡導推動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到改革開放初期的“傷痕文學”,再到近年來反映改革開放現實題材的一批力作,都充分證明廣東文學歷來都是探索者和弄潮兒。
我認為,今天的廣東文學處在一個繼往開來、再創輝煌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以鄧一光、魏微、葛亮等為代表的一批廣東優秀作家,深挖廣東作為嶺南文化發祥地、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開放先行地的特色創作資源,秉承嶺南文化敢為天下先的特質,進一步解放思想,大力推進文學觀念、內容、風格等創新,以“文學粵軍”的名號過長江、跨黃河,提升了廣東文學的美譽度和影響力。
廣東省作家協會創研部主任周西籬:
廣東文學正在努力朝著高峰攀登
我們看到,無論是魏微的《煙霞里》、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葛亮的《燕食記》,在全國的文學版圖上,是能夠占據一個重要位置的。
三位作家都是傾盡心力,完成了自己的“集大成”作品。從各種榜單、優秀長篇評選,以及新媒體平臺、圖書銷售平臺的不斷報捷顯示,這些作品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專家欣賞,讀者也喜愛。
我們認為,所謂“集大成”,是他們的藝術趣味和審美、敘事策略和哲學思考等的合成。因為他們以及其他優秀作家的存在,廣東文學正在努力朝著高峰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