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一部“史詩性”的文學拓荒之作 | 熊育群長篇小說《金墟》研討會在京舉辦
更新時間:2023-03-02 來源:十月文藝(微信公眾號)

2月27日上午,熊育群長篇小說《金墟》研討會在北京出版集團12層報告廳舉辦。此次研討會由廣東省作家協會、北京出版集團聯合主辦,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深圳出版社承辦。廣東省作協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張培忠,北京出版集團黨委副書記、董事、總經理吳文學出席會議并致辭。閻晶明、孟繁華、賀紹俊、胡平、陳福民、潘凱雄、梁鴻鷹、李一鳴、李舫、李朝全、李林榮、張莉、劉大先、楊慶祥、岳雯、叢治辰、李壯等知名作家、評論家與會研討。會議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主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胡曉舟作會議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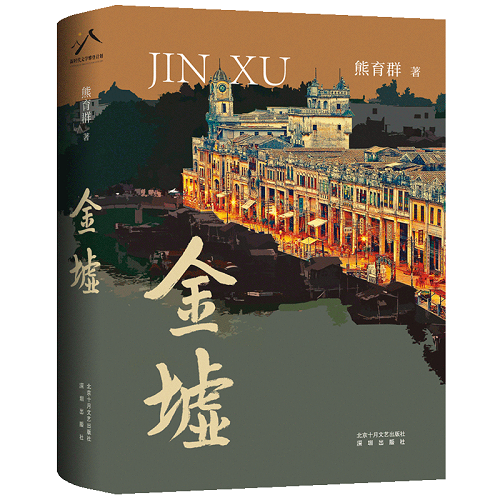

熊育群,湖南岳陽屈原管理區人。建筑工程師、新聞高級編輯、一級作家、教授,歷任出版社總監、報社總編輯、省作協副主席、省文學院院長、二級巡視員。獲得過魯迅文學獎、百花文學獎等,中宣部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現任中國作協散文委員會副主任。出版有詩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長篇小說《連爾居》《己卯年雨雪》,散文集及長篇紀實作品《春天的十二條河流》《路上的祖先》《一寄河山——大地上的遷徙》《西藏的感動》等20多部。作品被翻譯為英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阿文、印地文、馬來文、韓文、泰文、越南文、烏克蘭文等20余種語言出版。
《金墟》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項目,入選中宣部“2022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選題”,是熊育群創作生涯中難度最大的一次寫作,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說從僑鄉赤坎的旅游開發切入,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下,在一百多年、橫跨太平洋兩岸的宏大時空中,以司徒氏和關氏兩大家族代表人物為主角,展現全球視野下傳奇的人生與生活,以及跌宕起伏的命運;小說既有文化傳統賡續、社會變遷與生命歷程的書寫,又挖掘民族性和人性之光;兩個家族的歷史既是古鎮的歷史、華僑的歷史,也是廣東、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風云縮影,極具史詩性。

張培忠在致辭中表示,《金墟》以新時代鄉村振興為重點,在綿延一個多世紀、橫跨太平洋兩岸的時空中,展現中國農村的變革、家族的命運與民族的振興,是一部正面強攻當下現實題材的鮮活之作、厚重之作。小說由百年僑鄉赤坎古鎮的旅游開發計劃切入,以古鎮興衰與家族往事濃縮廣東、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風云,不僅是熊育群文學創作歷程中萃取眾長的成熟之作,更是書寫家國、振興鄉村的時代贊歌。

吳文學在致辭中表示,《金墟》是北京出版集團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重要作品。小說聚焦于著名僑鄉赤坎古鎮,以詳實的歷史細節和細膩的筆觸打通了虛構與非虛構的界限,融匯了過去和現在、海內與海外,重現了赤坎古鎮百年間的興衰起落,具有強烈的藝術表現力和文化浸潤力,是民族意識與世界意識的融合,是新時代僑鄉文學極具溫度與力度的一次創作,是一部深刻而具體地展現華僑及歸僑愛國、愛鄉、愛家精神的恢弘力作。
紀實與虛構并置的歷史和現實書寫
閻晶明評價《金墟》是一部很了不起的作品,剛一推出就進入了《長篇小說選刊》“第七屆長篇小說年度金榜”,得到了“揚帆計劃·中國文學海外譯介”的推介。熊育群以散文創作起家,后來又寫非虛構、小說,其創作的多樣性、多面性及創作的能力值得關注,《金墟》是他在這方面創作特點的集中體現。《金墟》既結合紀實與虛構,又融合歷史與現實,采用非線性交叉敘事,其產生的特殊效果不同于一般小說。“通過兩個家族百年的恩怨史,表達的是一種家國情懷,因此家族的恩怨和家國情懷主題的轉化和推出,也是這部作品非常有價值、非常值得去分析的地方。”
孟繁華感慨,《金墟》的特別之處在于小說跨度一百多年,從東方到西方,書寫司徒氏和關氏兩大家族,它讓我們看到歷史文化題材的豐富和無窮。創作這部作品時,熊育群本著誠懇的寫作態度,多次深入赤坎鎮甚至美國西部華僑的家里,因此《金墟》既有鮮明的寫真性,又有虛構的文學性。就小說和歷史之間的關系而言,是否如吉登斯所言“現代性就是歷史的斷裂”?孟繁華認為,《金墟》的這種講述,所證實的恰恰是歷史沒有斷裂,尤其在中國。
賀紹俊認為《金墟》是有難度的寫作,他看到熊育群寫作中的猶疑:小說是虛構的藝術,虛構與非虛構的關系又將如何處理?如何呼應銜接歷史與現實兩條線索?熊育群以奇數章寫現實,偶數章寫歷史,巧妙地引出兩個主題——重建古鎮的力度、難度,和古鎮的僑民文化、僑民精神。此外,賀紹俊對《金墟》中的兩個人物頗感興趣,一個是歷史中的司徒文倡,一個是現實中的司徒譽,“兩個人物面對困難背后的原因不同,但他們的精神又有共同之處。情懷和責任心可以說是僑民的文化精神,但更多的可能是一種民族的精神”。
潘凱雄說:“小說從內容來說是兩條線,一條是以開平碉樓為原型的保護問題,也是鄉村振興問題,另一條是華僑的問題,包括華僑的歷史、華僑的現狀等。這兩條線涉及歷史和現實、經濟和文化、國際和本土等諸多問題,這樣的復雜性客觀上對作者的統籌能力、結構能力、敘事能力都是巨大的挑戰,熊育群很好地完成了這個挑戰。”
楊慶祥用“虛構和非虛構的關系”“歷史與當下的關系”“到世界去和尋根”等幾個方面闡述了閱讀《金墟》的感受。“海量的材料如何轉化成長篇小說,赤坎建城史如何與當下聯系?熊育群巧妙地以調查者、講故事的人兩種聲音把材料和敘述融合在一起,以塑造司徒家族兩個關鍵人物形象的互動展現中國式現代化,為寫作者提供了借鑒和示范意義。”
岳雯認為《金墟》是一部給人以真實感的小說,我們從中獲得了僑民歷史、以鄉村振興思路經營古鎮等方面的知識,由此對于僑民生活有了非常全面的了解。同時,《金墟》也是一部描寫性的小說,作品充滿景觀化的景象,這也許與作者的建筑學經歷有關。此外,《金墟》也是一部多種真理并存的小說,其可貴之處在于讓不同聲音、真理互相碰撞,讓讀者在權衡中做出思考和判斷。
古鎮建筑與民俗文化的復蘇
胡平指出《金墟》很重要的貢獻在于重新發現了赤坎這座百年古鎮,小說是復調的,著重書寫了興于民國十五年和新時代的兩次赤坎城鎮建設,以司徒氏兩代人、主要是司徒文倡和司徒譽兩位代表性人物貫穿起來,寫出了兩代城建的艱難和業績。“這是一個頗難駕馭的題材,但熊育群的把握相當老練。在敘述上,作者對文體風格和節奏的掌控不疾不徐,文字上不顯過于累贅,也不顯過于簡略,這本身是一種力量。”
李一鳴表示,熊育群以文學的力量打造文學建筑學中一座極為厚重浪漫、包含深厚文化底蘊、金光閃閃的“金墟”。小說具有史詩般的力量,寫出百年社會變遷史和僑鄉兒女的心靈史,深刻展現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挖掘現實生活背后、歷史更迭中人心和人性的深意。在他看來,《金墟》也是一首抒情長詩,作品在意味、細節等方面非常突出,用鐘聲、騎樓、碉樓、圖書館等獨特的意象,成就了意象叢生、非凡絢麗的錦繡華章。
李舫認為赤坎是中國獨特的存在,它處于中國改革開放前沿地帶但又不是十分發達,正因為它在前進和保守間的糾結,才有了巨大的敘事張力。熊育群筆下豐滿的人物形象、兩代人艱難的創業故事、獨特的文化意象“碉樓”、有趣的民生民俗細節等,讓小說充滿真實、動人、感人的力量。雖然《金墟》的題材非常難駕馭,但作者以筆和腳步丈量土地,老練地把握敘事風格,作品引人入勝,體現出熊育群對嶺南文化、僑鄉文化深刻的觀察和思考。
李朝全用“虛與實”“小與大”“今與古”“內與外”四個方面分析,認為小說既有百年來的歷史積淀、歲月積淀,同時又有碉樓、騎樓這些文化符號的涅磐與重生。他還表示,《金墟》創造了非常鮮明、頗具鋒芒的基層干部形象,并以飽滿的情感生活描寫使之形象立體。“作為一個在廣東生活多年的湖南籍作家,熊育群對廣東方言和地方知識的自如運用,對廣府文化、疍家文化、僑鄉文化的開掘和弘揚,都是這部小說不可忽視的長處。”張莉感慨,《金墟》這部作品特別有意思的地方是,它重新讓我們認識了赤坎,赤坎并非荒廢之地,而是連接起歷史、此刻和未來的地方。“本來這個建筑是固定的,但是他通過情感的流動和回憶的流動,使金墟變成今天非常具有生命和活力的文學地標,《金墟》在這方面給我們帶來很新的視角。”此外,張莉認為《金墟》在寫作過程中逐漸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找到了兩難情感的平衡點。
李壯從《金墟》和《平安批》的比較中闡釋了自己的閱讀感受。他認為,陳繼明《平安批》以動寫靜,因為寄托物是批、信,《金墟》則以靜寫動,因為寄托物是樓,由此引出或者發散出人的遷徙和奮斗。《金墟》里面有一種動與不動的辯證,結合了鄉土中國和世界中國兩種書寫方式,通過對騎樓等建筑裝置的刻畫,完成了從家族到民族、到國家的小說主題的轉化。
國際視野下的僑民文化與家國情懷
陳福民認為,《金墟》的明暗雙線結構,實際上給中國近現代史注入了非本土的元素。熊育群將被遮蔽的無名歷史和材料揭示出來,賦予作品以國際視野,并在寫作中融入自己對中國歷史諸多的反思、憂慮,特別是史實和虛構兩條線索的結合處理得非常理想,尤其是虛構做到了了無痕跡,讓人虛實難分。“《金墟》對于當下的小說創作提供了不少新鮮的經驗,特別是在歷史材料的處理上,宗法制與土地的關系,以及宗法植根之深,對于中國現代改革的困擾,他書寫得非常到位。”
梁鴻鷹提出,廣東與中國近現代歷史密切相關,講好這個故事,是書寫中國故事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作家熊育群畢業于建筑工程系且做過很長時間的記者,在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同時,擁有深入生活、深入群眾的經驗,這使得這部作品令人信服。他還表示,“《金墟》的立足點當然還是在當下。我們歷史上有那么多苦難、那么多文化積累,這些東西在新時代、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到底如何重新煥發新的光彩,這是作品的立足點所在”。
李林榮評價《金墟》是挑戰長篇小說創作多重困難的厚重之作。“僑鄉的歷史,僑鄉在現當代城鄉建設的特殊歷程,以及海外華人奮斗史等,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段歷史,《金墟》恰好為此處史實材料繁雜卻文學表現稀缺的領域提供了補充,在這個意義上,《金墟》是矗立在現當代文學的拓荒地上的一部重要作品。”
劉大先認為,《金墟》特別重要的貢獻在于它揭示了司徒文倡、司徒譽為代表的兩種現代化途徑,《平安批》寫的是東南亞海上絲綢之路的記憶,而《金墟》填補了和北美之間絲綢之路的記憶空白。此外,劉大先指出小說首尾呼應的鐘聲是非常有意思的隱喻,“《金墟》實際上是一部文化遺產的展演,它告訴讀者歷史也在前行,正在前行當中,歷史當中的人背負歷史和現實向前探索”。
如何在鄉村振興、鄉村建設的大主題中拓路?叢治辰認為這是熊育群面臨的挑戰。《金墟》的成功創作得益于作家本人對題材的敏銳把握,“《金墟》終于在主題寫作中打開一個國際化、全球化的視野,它不僅是在中國寫鄉村變化,而是在更宏大的世界背景下寫鄉村變化,這是這部小說特別富有創造性的地方”。
熊育群對主辦方和各位專家在文學理論上的指導和歸納、見解上的梳理和發現表示由衷感謝。他坦言,“這是我人生中最難的一次寫作,我也是有一點野心,希望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就像著名作家陳忠實說的,想寫一部墊枕頭的書。《金墟》的題材非常好,我好像抓到一個寶貝,時間跨度一百多年,空間從中國到北美大陸,非常復雜,光是小說結構就想了兩個多月。《金墟》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對此我深表謝意。”
深圳出版集團總編輯、深圳出版社社長聶雄前在發言中表示,熊育群在極具史詩性的長篇巨著中,以優美的語言和形散神聚的筆法書寫華僑的命運、華僑對改革開放的貢獻以及華僑對故土的眷戀,可稱其為廣東、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風云的縮影。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金墟》責任編輯胡曉舟作會議總結,感謝專家們就熊育群長篇小說《金墟》發表的精彩見解,“與會的領導和專家一致認為《金墟》是一部面向現實、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重要收獲。在這部作品中,作者立足當下,把百年赤坎古鎮置于廣闊的時空背景中,在充分反映古鎮興衰變遷史的同時,也寫出了鄉村振興政策下古鎮的新發展。祝愿熊育群老師今后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為讀者提供更加豐富的精神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