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羅昕 | “非虛構”寫作:現實關懷與文體創新
更新時間:2022-11-29 作者:羅昕來源:澎湃新聞
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諾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軍》《劊子手之歌》、湯姆·沃爾夫的《電冷卻器酸性試驗》……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非虛構”作為一種文體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
而在中國,如今這一文體也備受讀者與學界關注。2010年,楊爭光的《少年張沖六章》、梁鴻的《中國在梁莊》等作品引起了《人民文學》時任主編李敬澤的注意。那一年,《人民文學》雜志開辟了名為“非虛構”的新欄目,并啟動“行動者計劃”,吁請海內外寫作者走出書齋,走向現場。從此,“非虛構”在中國不僅是一個學術名詞,還是一個日漸廣泛的寫作實踐,覆蓋的寫作群體越來越大。
11月24日,由江蘇省作家協會和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第六屆中國當代文學揚子江論壇在南京舉行。本屆論壇以“廢墟與非虛構:現實關懷與文體創新”為議題,除了廣邀學者,還請來了孫甘露、李洱、徐則臣、葉舟、喬葉、路內、魯敏、孫頻等小說家。來自全國各地的約50位文學中人以線下或線上方式參與研討。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表示:“當我們談到‘非虛構’,常常談到‘真實’,但我們容易忘記‘真實’既是客觀的,也和人的知識結構、認知結構密切相關。因而,抽象地談論哪一種文體更真實意義不大,真正的意義在于非虛構在這個時代到底體現了我們認知結構怎樣的調整,以及我們為何認為這樣的調整可以讓我們更好地去把握這個時代紛繁復雜的現實。”

11月24日,第六屆中國當代文學揚子江論壇在南京舉行。

李敬澤
每個小說家都有強烈的非虛構動機
不少小說家提到,在中國文學現場,虛構和非虛構已然相互滲透,邊界不太明晰。非虛構作品對傳統的小說創作造成了沖擊,但也帶來了豐富,比如在方法和美學上提供了很多借鑒。
“我本人的《花腔》,也可以夸張地說是用非虛構形式完成的虛構作品。”李洱說,小說的人物、情節是虛構的,但每個小說家在文本之外都有非常強烈的非虛構動機,這種動機能賦予作品很強的現實感,“馬爾克斯也認為他的作品帶有強烈的非虛構特征。他和傳記作者提過,他作品里的每一個細節和人物都是真的。”
李洱提到,《百年孤獨》在中國出版時很薄,但馬爾克斯說,和他的每部小說一樣,應該把查閱的資料目錄附在后面,而這些資料目錄至少應該與小說文本一樣厚。“小說家在內心里會強調自己的非虛構特征,只有在打官司的時候才會說他的作品完全是憑空虛構的。”
喬葉回憶自己寫《拆樓記》,出單行本時總被媒體追問“非虛構小說”這一標簽有何特殊意義。“我還是沒辦法充分回答這個問題。拆樓事件很容易被概念化,我就想呈現出事件背后被遮蔽的人心和人性,而小說技法可以作為一把利刃插入事件的縫隙,使敘事效果更為趨真。”
在她看來,藝術上的“真實”就是讓人相信——讓自己相信,也讓讀者相信。“我理解的這個真,通常說是藝術的真。藝術的真來自生活的真,還有寫作者手寫我心,捫心自問的真,這幾個真糅合在一起。這是很核心的標準和道德。”她說,“博爾赫斯說強大的虛構產生真實,那么孱弱的非虛構也能造成虛假。你呈現出來的到底是真實還是虛假,說到底要看作家的力量。”
“我們看見的是作品,作品背后的東西往往是看不見的。但這個時代的風向深深影響了這個時代的文學創作和研究。”孫甘露想起了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里的一句話——“一個時代的藝術精神風尚就像旗幟,你看見旗幟在飄,實際上是風在吹”,“作品背后的那個東西,那個根本的、本質性的力量,才是作家和批評家對于一個時代的認知和思考。”
過寬的定義可能忽略文體真正的價值
這一次論壇還突出了一個現象,即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甚至批評家與批評家之間,大家對于非虛構的定義和理解依然很不一樣。如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丁帆所說:“它一直是在學理的界定中,沒有經典化。”
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歸納西方的非虛構文學有五個特征:一是現實性,即為現實題材,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二是親歷性,即寫作者是事件的親歷者,不能僅僅通過資料查閱完成寫作;三是見證性,見證了特定歷史時段的時代變遷,而非完全的私人化;四是個人性,寫作者對于人性、社會、歷史等的評價基于自己的感受,不受外力影響;最后是文學性,主要體現在大量的生動的細節呈現,這一點是非虛構文學和新聞報道的主要區別。
在他看來,學界需要辨認非虛構和過去的紀實文學、報告文學等有何區別。目前人們有關非虛構的定義過于寬泛和混亂,許多討論沒有交鋒,更沒有意義。他希望這次論壇可以推動共識。
杭州師范大學教授洪治綱表示,中國的非虛構寫作在這十幾年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范式,呈現出兩大特點。一是不僅追求共情,還追求共理;二是創作者多重身份的介入。比如寫《中國在梁莊》的梁鴻不僅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故鄉人,一個知識分子;寫《野地靈光》的李蘭妮不僅是一個作家,也是抑郁癥患者和精神病史的反思者。他并不認同歷史題材就不屬于非虛構寫作,“比如阿來寫《瞻對》,他顯然是歷史的尋訪者,也是作家,多種身份的介入構成了作品的復雜性。”
人民大學教授楊慶祥同樣認為文學界需要對非虛構和固有文體作出區分。作家可以不考慮這些,但學者需要對此界定。很多人已忽略非虛構的最基本前提——必須要做嚴格的社會學調查,有大量的樣本和案例采集,并進行定量分析,但中國目前絕大部分非虛構寫作在這方面沒有“過關”,導致非虛構文體被侵蝕。“就像1980年代前后非常興盛的新新聞寫作,還有紀實文學寫作,無不曇花一現,因為一旦把文體的邊際消除了,它們真正的價值也就被忽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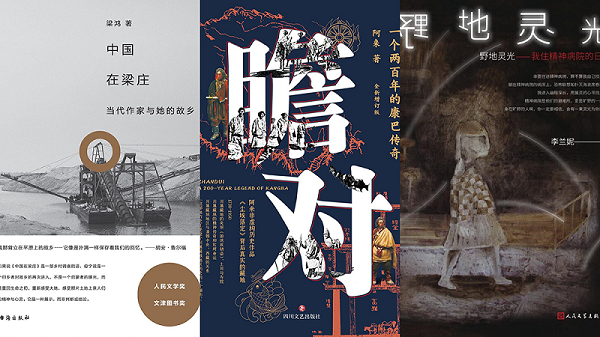
真正的公認佳作,似乎還沒有出現
“回頭想一想,我們現在談中國非虛構,談所謂的代表作,依然還是那幾部——梁鴻的梁莊系列、阿來的《瞻對》,還有李娟和袁凌的作品。”
徐則臣也是當年《人民文學》負責非虛構欄目的編輯之一。他直言:“十幾年過去,我們預期中的、真正的公認佳作,似乎還沒有出現。”
在他看來,一方面,像一些學者說的——非虛構的定義過于寬泛,什么文本都能往里放,另一個方面,起碼在文學期刊上,人們對于非虛構的理解又是狹隘的。比如一談到現實關懷,很多人就只想到了“底層”“鄉村”“苦難”等等。而且,同樣是苦難敘事,人們對非虛構顯然比對虛構“寬容”。“如果把《第七天》里的細節以非虛構的方式寫出來,我們還會像當時那樣對它特別挑剔嗎?我們現在對于非虛構寫作的要求還是低了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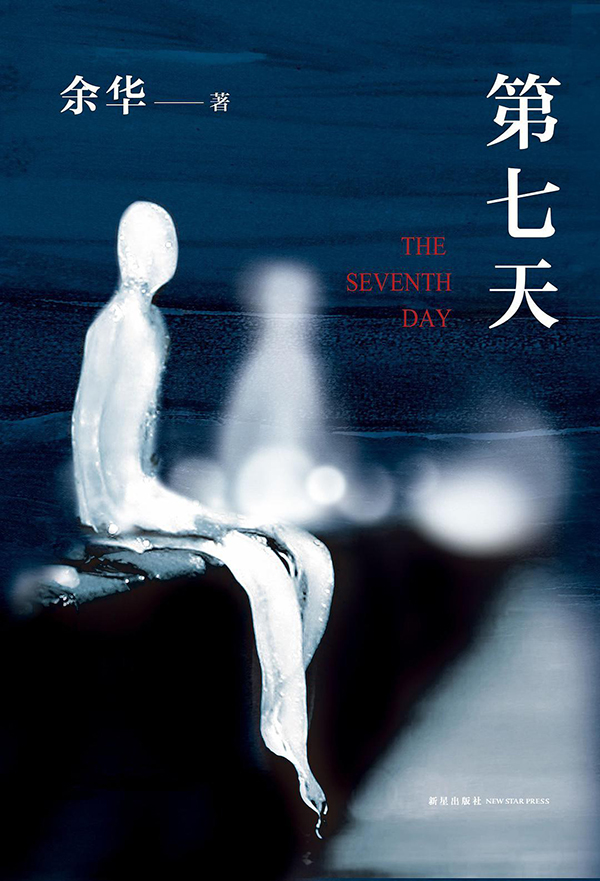
作為一名小說家,徐則臣也認為虛構與非虛構的區分對創作本身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實現更好的寫作效果。他最近愛看聊齋,文本里是絕對的虛構,但它依然能實現對社會的批判,以及極好的現實感。“在功能上,它可能對非虛構寫作 ‘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現在的很多非虛構作品也未必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清華同樣認為非虛構并不存在特殊的優越性,它只是處理和關照現實的一種方法和角度,寫作者的態度、素養與能力才至關重要。而且,面對一部非虛構作品,人們首先要追問的是它為何而寫?“有的寫作是為了獲獎,有的寫作是為了資本,這樣的非虛構缺乏人文精神和價值,所承載的現實反而更是虛假的。我們對此不能推波助瀾,反而要有清醒的認識和反思。”
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畢飛宇認為,虛構與非虛構的關系是二律背反的。“如果我們承認修辭的局限,那么,我個人的體會是,在虛構的極限處,虛構會走向非虛構。同樣,非虛構到了極限,非虛構就必然會依仗虛構。”
在虛構與非虛構這個問題上,畢飛宇坦言對他啟發最大的是溫克爾曼。“古希臘的雕像是典型的非虛構,古希臘的人體雕塑與真實的人體甚至可以互換。然而,古希臘人對人并沒有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神,他們熱衷的是對神的表達和神的想象——也就是虛構。然而,這種想象又有一個依據,那就是人,通過對人體的非虛構完成了對神的虛構。”在畢飛宇看來,即使在今天,古希臘的藝術對虛構與非虛構都會給我們帶來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