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biāo)題

標(biāo)題
內(nèi)容
名家新作聚焦粵港澳題材寶藏,共筑大灣區(qū)文學(xué)版圖蔚然氣象
更新時間:2022-08-15 作者:黃楚旋來源:南方日報
“在這席間,可聞得十三行的未涼余燼,亦聽見革命先聲的篤篤馬蹄。他閉上眼,用上了一把力氣,只管將這味道與聲響,都深深地揉進(jìn)手中的餅餡……”
在作家葛亮最新推出的長篇小說《燕食記》中,中國文化傳統(tǒng)里“常與變”的辯證博弈,植根在了嶺南一對師徒身上。沿著嶺南飲食文化的發(fā)展脈絡(luò),《燕食記》書寫了粵港兩地飲食故事,生動描摹中國近百年社會變遷、世態(tài)人情的雄渾畫卷,被譽(yù)為“呈現(xiàn)粵港澳歷史文化版圖的精心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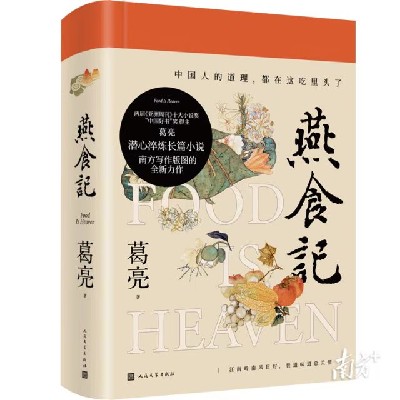
《燕食記》
近年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qū)建設(shè)的不斷深入,大灣區(qū)文學(xué)共建也日益受到多方關(guān)注,許多作家、評論家先后對此展開研究、書寫與探討。從著眼粵港飲食故事的《燕食記》、以“眼鏡之都”深圳橫崗為背景的《你的目光》、首部全景式展現(xiàn)東深供水工程建設(shè)的長篇報告文學(xué)《血脈——東深供水工程建設(shè)實錄》,到蓬勃發(fā)展的《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學(xué)評論》期刊等,眾多知名作家、評論家正共同構(gòu)筑大灣區(qū)文學(xué)版圖的蔚然氣象。
以“飲食”為“容器”編織粵港傳奇
葛亮仍清晰記得,20年前從內(nèi)地來香港讀書時,族中長輩首次帶他上茶樓飲早茶時的場景。“我是真被這熱鬧的氣象所吸引,像是瞬間置身于某個時光的旋渦。”
數(shù)十年前,葛亮祖父年輕時來粵飲茶,也是相似場景。時光荏苒,那間茶樓人事迭轉(zhuǎn),但總有一股子精氣神超越時空而久久縈繞不散。
早在寫《北鳶》時,葛亮就借書中人物之口,道出這樣一句話:“中國人的那點子道理,都在這吃里頭了。”這個主題在他心中一直揮散不去,念念不忘。

葛亮近照
都說“食在廣東”。屈大均在《廣東新語》里曾寫道:“天下所有美食,粵地幾盡有之。”反之,“粵地所有美食,天下未必盡也。”嶺南,以其包容、自由開放的文化特性聞名全國,天南地北的文化在此流轉(zhuǎn)遷徙、開枝散葉。體現(xiàn)在飲食上,則是不同菜系之間交纏、相匯,造就海納百川的文化氣象。這便成為葛亮切入小說創(chuàng)作的原因:“嶺南的飲食文化結(jié)構(gòu),其實是非常好的有關(guān)于歷史、文化、民生,乃至于社會結(jié)構(gòu)的一個容器。”
一個人的個人記憶可以被食物所重現(xiàn),一段浩大的歷史也可以由食物所見證。飲食,便成為時代磨礪中的一枚切片。到港生活20年后,葛亮憑借這一質(zhì)地渾厚、帶著日積月累的苦辣酸甜的切片,不斷親近嶺南文化的內(nèi)質(zhì)和肌理,最終融入其中。他坦言,創(chuàng)作《燕食記》,不僅依靠大量案頭工作、田野調(diào)查,還需要“情感層面的準(zhǔn)備”。
“穩(wěn)中求變”,是葛亮對嶺南文化的理解,“可能中間會有一些掙扎,中間演變的過程中伴隨著陣痛,但是它總是會煥發(fā)出一種新鮮的力量。”這也成為他筆下角色命運流轉(zhuǎn)的一根暗線:師傅榮貽生系茶樓主要做禮餅的“大按”,技藝過人;徒弟陳五舉則一度“叛師門”成為本幫菜廚師,經(jīng)歷了“變則通,通則久”的人生起伏。小說以師徒二人的傳奇身世以及薪火存續(xù)作為線索,串起辛亥革命以來粵港經(jīng)歷的時代風(fēng)云變遷。
“在熟悉香港這座城市的過程中,我也在探訪著它與嶺南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在葛亮眼中,香港的城市結(jié)構(gòu)、氣性十分特別。人們印象中的香港,更多是維港璀璨、都市繁華,但他認(rèn)為,香港也有十分古典、與中華傳統(tǒng)文化禮俗一脈相承的一面。
以飲食為題,最終講的還是世道人心。葛亮認(rèn)為,飲食是活的文化,不斷革新、適應(yīng)口味,既是時間流轉(zhuǎn)的表達(dá),也是空間演變的傳遞。而茶樓,很好地代表了內(nèi)地和香港文化之間的同氣連枝。如他所說:“在這個文化場域里,我們?nèi)阅芸吹街腥A傳統(tǒng)文化的保存與延續(xù),而香港故事,也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舊時風(fēng)情與潮流前沿的交相輝映
豪華大樓里充斥著時尚生活,但走到小巷深處,卻能在不經(jīng)意間,瞥見古老傳統(tǒng)延續(xù)的痕跡……著名評論家謝有順曾以此為例,形容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化上尤為突出的特性:在同一空間結(jié)構(gòu)內(nèi),多重時間“并置”,構(gòu)成多面的灣區(qū)呈現(xiàn)。
“文化傳承最重要的載體是日常生活,只要有一種生活方式還在,沒有被顛覆,文化就還在。”謝有順認(rèn)為,寫出對日常生活的傳承,書寫時間和空間里“并置”的作品,粵港澳作家大有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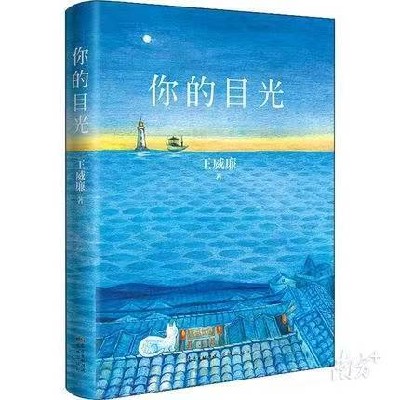
《你的目光》
在葛亮用小說著力描摹嶺南傳統(tǒng)生活經(jīng)驗與舊日風(fēng)情的同時,許多作家也對大灣區(qū)這片土地上日新月異的社會面貌深感興趣。來自西北的青年作家王威廉,在廣州生活已20余年。最近,他的新作《你的目光》,就以廣州和深圳為小說背景,以深圳橫崗——一個生產(chǎn)了全世界七成眼鏡的“眼鏡之都”為線索,書寫年輕一代設(shè)計師的生活、情感與創(chuàng)新,反映出年輕一代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的心氣,同時也折射出廣州、深圳等粵港澳大灣區(qū)城市的深厚文化底蘊(yùn)與不斷創(chuàng)新的勃勃生機(jī)。
“一個作家不可能逃開環(huán)境對寫作的影響,所有的創(chuàng)作或創(chuàng)新都離不開已有的文化資源。”王威廉說,在嶺南地區(qū)多年的生活經(jīng)歷使他了解到嶺南的客家與疍民這兩大群體,在《你的目光》里,男、女主人公分別被設(shè)定為有著客家和疍家的文化背景,讓作品更增添了一層民俗學(xué)、文化學(xué)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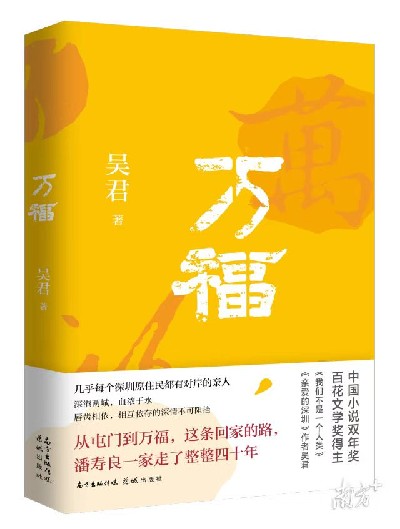
《萬福》
深圳作家吳君則憑借《親愛的深圳》《皇后大道》《萬福》等作品與深圳一同成長。其中,長篇小說《萬福》講述了深圳萬福村阿慧和陳水英兩個家庭三代人四十年的往事,與深圳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變遷息息相關(guān),也展現(xiàn)了深圳與香港這兩座城市之間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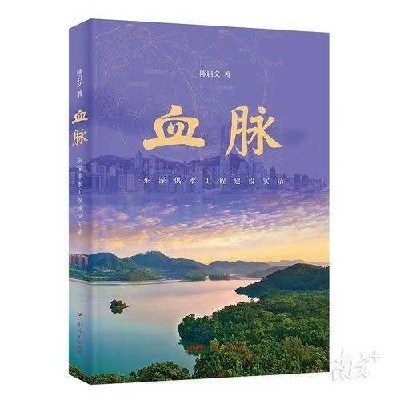
《血脈——東深供水工程建設(shè)實錄》
不僅僅是小說,在長篇報告文學(xué)《血脈——東深供水工程建設(shè)實錄》一書中,作者陳啟文通過田野調(diào)查,抵達(dá)當(dāng)年的一個個施工現(xiàn)場,追蹤采訪工程的建設(shè)者和守護(hù)者,還原了東深供水工程各個建設(shè)時期的艱辛歷程。東深供水工程時間跨度近60年,陳啟文說,他用類似多重奏的文章結(jié)構(gòu),串聯(lián)起不同時期的歷史,旨在表現(xiàn)“共飲一江水,粵港兩地情”的主題。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還有不少新銳作家陸續(xù)嘗試以往較為少見的先鋒、實驗寫法,不斷拓寬大灣區(qū)題材“怎么寫”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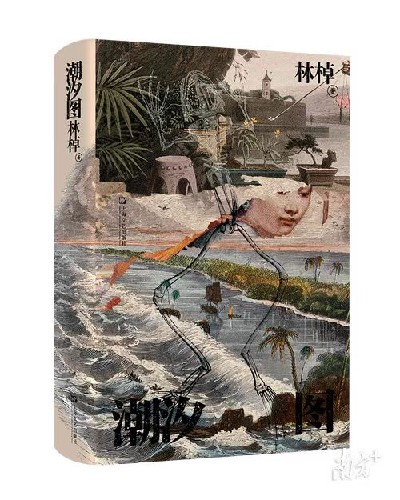
《潮汐圖》
同樣今年出版的還有青年作家林棹長篇小說《潮汐圖》。小說的主角是一只游歷四方的雌性巨蛙,從珠江水上人家,到廣州十三行,從澳門奇珍園,再到茫茫重洋,小說通過這樣一個充滿嶺南風(fēng)土特色的魔幻故事,將近代中西文化交匯的歷史緩緩鋪陳開來。評論家唐詩人評價稱,該書通過另辟蹊徑的視角和天馬行空的想象力,為書寫同類型題材找到了新的切入口。
挑戰(zhàn)與機(jī)遇并存,孕育本土文學(xué)增長點
葛亮感慨稱,大灣區(qū)文學(xué)題材有著極大的空間感和包容性,讓每個作者都能在其中找到情感落點,可能是文化的、歷史的、語言的。文化在求新求變的構(gòu)成中,為寫作者提供了不斷深入挖掘、觀察的巨大空間。
“大灣區(qū)是一座尚未得到充分發(fā)掘的文學(xué)富礦。”廣州市評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李德南指出,大灣區(qū)建設(shè)有著更為內(nèi)在的驅(qū)動力——全球化進(jìn)程的推進(jìn),作為對現(xiàn)實的藝術(shù)化再現(xiàn),大灣區(qū)文學(xué)所涵蓋的當(dāng)代性歷史經(jīng)驗與現(xiàn)實經(jīng)驗也是極為豐富、廣闊的,對寫作者的觀察、思考和寫作都提出更高的要求。
關(guān)于紛繁復(fù)雜的灣區(qū)題材向?qū)懽髡甙l(fā)出的挑戰(zhàn),青年作家王威廉是這樣理解的:“大灣區(qū)文學(xué)”是超乎具體的地理空間的,它更加抽象、更加具有可建構(gòu)性。與此同時,大灣區(qū)各城市在文化特質(zhì)與發(fā)展驅(qū)動上,既有“同”的一面,也存在“異”的一面。也正是在“同”與“異”之間,歷史的豐富性獲得極大的滋養(yǎng),也不斷凝鑄和塑造著新的文化精神。
王威廉認(rèn)為,“大灣區(qū)文學(xué)”包含著全球化進(jìn)程下寫作者所面臨的普遍性困惑與機(jī)遇。“在這個精神空間中的寫作,肯定不會只是一種文化、地理層面上的民俗展示,它一定會觸碰到那些極為重要的歷史關(guān)節(jié),而不是僅僅停留在一個創(chuàng)作概念上。”王威廉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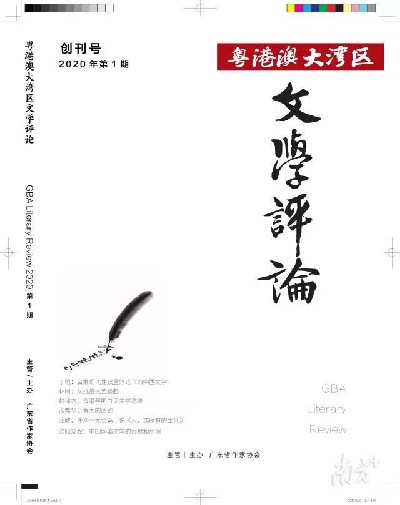
《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學(xué)評論》
與此同時,暨南大學(xué)中文系副教授、評論家龍揚(yáng)志提出,創(chuàng)作者的文學(xué)經(jīng)驗往往基于一城、一地的生活感性,來自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的作家、詩人,可能習(xí)慣在既有的文化空間里寫作,未必自動獲得新的文學(xué)內(nèi)涵,唯有當(dāng)生活在大灣區(qū)的人們通過創(chuàng)業(yè)、棲居等方式,對珠三角多元、開放、包容的嶺南文化、都市文化、海洋文明產(chǎn)生發(fā)自內(nèi)心的認(rèn)同,才能進(jìn)一步突破城市文學(xué)的邊界,形成真正具有全新內(nèi)涵和價值理念的“大灣區(qū)文學(xué)”。
無論如何,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學(xué)題材已經(jīng)逐漸顯現(xiàn)出巨大的創(chuàng)作潛力,進(jìn)而成為廣東本土新的文學(xué)增長點。近年來,廣東省作協(xié)突出“構(gòu)建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學(xué)”特色品牌,“前沿性”“日常性”“豐富性”,是廣東省作家協(xié)會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張培忠對部分大灣區(qū)文學(xué)作品的總結(jié)。他認(rèn)為,當(dāng)代灣區(qū)青年作家思想解放、意識超前,秉承廣東文學(xué)兼收并蓄、敢為人先的進(jìn)取精神,展現(xiàn)出務(wù)實、開放、兼容、進(jìn)取的廣東作家新風(fēng)貌。“未來,廣東作協(xié)將繼續(xù)倡導(dǎo)廣東作家講好大灣區(qū)故事,創(chuàng)作更多接地氣、有溫度、有深度的嶺南文學(xué)精品力作。”
專家點評
粵港澳作家群如何從大灣區(qū)的歷史、文化和當(dāng)下的生活經(jīng)驗中汲取養(yǎng)分,講好大灣區(qū)故事,展現(xiàn)新時代大灣區(qū)開放包容、創(chuàng)新奮進(jìn)的文化形象與獨特魅力?中山大學(xué)中文系日前在穗舉辦了“大灣區(qū)文學(xué)可能性”論壇,特邀香港作家唐睿、廣州青年評論家李德南、唐詩人等嘉賓,共同展開深入探討,這里節(jié)選部分精彩發(fā)言,以饗讀者。
香港作家、浸會大學(xué)中文系助理教授唐睿:
粵港澳文藝互動淵源值得進(jìn)一步探索
香港文學(xué)中的廣東元素,早期值得一提的就是作家黃谷柳的《蝦球傳》。從小說里我們可以看到,廣東和香港在文化、歷史、地理上都是相連的,粵港向來就有血脈相連的概念,這在上世紀(jì)40年代的香港文學(xué)里,是比較普遍的共識。在侶倫的《窮巷》,還有舒巷城的小說等早期作品里,也常常能看到這種兩地在文化歷史上互連融通的呈現(xiàn)。
改革開放后,許多年輕作者通過各種機(jī)會到內(nèi)地游歷,足跡遍布各地。從中誕生的游記,記錄了他們對內(nèi)地改革開放之初的種種觀察,既有宏觀的社會記錄,又包涵了微觀的民生素描,作者的文化經(jīng)驗既立足于中華文化傳統(tǒng),但同時又通過略帶距離的目光來解讀內(nèi)地風(fēng)土人情,為各地的山川名勝賦予有別于傳統(tǒng)的意義,其中也記錄了香港人對自己身份認(rèn)同和文化背景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港人也有著很豐富的廣東生活經(jīng)驗,比如很多來港打拼的潮汕人,港人為內(nèi)地學(xué)校捐錢支持“希望工程”、香港志愿者去粵北地區(qū)扶貧,還有惠州東江縱隊和文化名人大營救的故事等,這些歷史淵源都值得香港作家進(jìn)一步關(guān)注、探索和開發(fā)。實際上,在全球化語境下,粵港澳之間既相似又各有特色的文化傳統(tǒng),有非常多的細(xì)節(jié)和空間可供作家進(jìn)行發(fā)揮。
暨南大學(xué)中文系副教授、青年評論家唐詩人:
大灣區(qū)作家需要有世界視野和未來意識
粵港澳大灣區(qū)作為城市群,從文學(xué)角度來看,建設(shè)“人文灣區(qū)”,可以理解成拓展大灣區(qū)城市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研究。結(jié)合當(dāng)前大灣區(qū)作家的創(chuàng)作實踐,我以為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來展開思考。
第一是圍繞嶺南文化,探索粵港澳大灣區(qū)城市的歷史淵源和文化脈絡(luò)。大灣區(qū)城市是相互毗鄰的城市群,它們在歷史、文脈、語言、習(xí)俗上都有著清晰的共通性。最近兩年,《雄獅少年》《醒·獅》《白蛇傳·情》等現(xiàn)象級作品的涌現(xiàn),對于我們思考嶺南文化的創(chuàng)新表達(dá)和當(dāng)代價值帶來了很好的啟發(fā)。
第二是文明敘事問題,這包括中西方文明和城鄉(xiāng)文明敘事。粵港澳大灣區(qū)的澳門、廣州、香港等,這些都是中國近現(xiàn)代以來最直接遭遇中西方文明交流與沖突的城市。香港作家西西的《我城》《飛氈》等,對這段歷史文化有所觸及。
第三個是大灣區(qū)的城市書寫問題,包括城市新移民敘事、城市景觀書寫以及城市未來想象等,以此折射當(dāng)代中國城市化歷史進(jìn)程。世界性、海洋性是大灣區(qū)文學(xué)的內(nèi)在特征,這意味著灣區(qū)作家需要有一種世界視野、未來意識。這方面,王威廉的《野未來》《你的目光》等系列小說,關(guān)注科技發(fā)達(dá)時代城市人的生活可能和精神歸宿問題,具有一種普遍的關(guān)照意味。
廣州市評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青年評論家李德南:
生活的流動性將成為文學(xué)書寫重點
從地域、區(qū)域的角度來看,大灣區(qū)是一座尚未得到充分發(fā)掘的文學(xué)富礦。很重要一個原因在于,全球化進(jìn)程的推進(jìn),是大灣區(qū)建設(shè)更為內(nèi)在的驅(qū)動力,因此,大灣區(qū)文學(xué)具有極為豐富、廣闊的當(dāng)代性歷史經(jīng)驗與現(xiàn)實經(jīng)驗。
廣州、澳門、香港、深圳等城市,得風(fēng)氣之先,產(chǎn)生了很多新的生活經(jīng)驗。這些新經(jīng)驗又是發(fā)散式的,對中國的許多地方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先后出現(xiàn)了打工文學(xué)、新城市文學(xué)、科幻文學(xué)等文學(xué)潮流,它們是對中國新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直接表達(dá)。
在現(xiàn)代社會中,人的流動成為常態(tài),寫作也是如此。鄧一光、鮑十、王十月、葛亮、盛慧、塞壬、王威廉、蔡東、鄭小瓊、畢亮等作家,現(xiàn)在都在大灣區(qū)生活,但是他們又都不是土生土長的本土作家。他們的寫作,都有對這種流動的生活經(jīng)驗的表達(dá)。他們的寫作,自然也是大灣區(qū)文學(xué)的重要構(gòu)成部分。
廣東省作家協(xié)會理事、廣州市作協(xié)副主席陳崇正:
高學(xué)歷人才聚集是大灣區(qū)文學(xué)一大優(yōu)勢
在我看來,有三個維度拓寬了廣東文學(xué)的可能性。
第一個是教育。廣東這些年有一批青年作家異軍突起,在全國文壇的表現(xiàn)都非常亮眼。這里面當(dāng)然有經(jīng)濟(jì)騰飛、人口流入,凝聚了文學(xué)人才的因素,同時也受惠于21世紀(jì)以來的大學(xué)擴(kuò)招,使得一批批具有文學(xué)才能的人進(jìn)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文學(xué)人口的擴(kuò)大為文學(xué)生產(chǎn)提供了人才基礎(chǔ),現(xiàn)在大灣區(qū)的作家,碩士、博士比比皆是,這是一大特點。
第二個是媒介。互聯(lián)網(wǎng)和新媒體的發(fā)展,打破了原來紙刊所形成的文學(xué)資源壁壘。網(wǎng)絡(luò)出現(xiàn)以后,文學(xué)上的交流、交鋒來得非常直接。媒介的發(fā)展,也讓廣東文學(xué)在媒體傳播上獲得了新的動能。
第三個是科技。在大灣區(qū)寫作,幾乎無法回避的一個話題就是科技發(fā)展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和改變。近些年來,廣東有很多作家開始創(chuàng)作帶有科幻元素的作品,開始關(guān)注人類未來,這正是時代氣象的表現(xiàn)。無論是大灣區(qū)文學(xué),還是最近引起熱議的“新南方寫作”,往往是有了這些文學(xué)概念的召喚,才會倒逼作家去反思自己的寫作資源和題材優(yōu)勢,從而開拓出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