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nèi)容
楊湯琛|《三十六騎》是如何超越雅俗之界的
更新時間:2021-02-01 作者:楊湯琛來源:光明網(wǎng)-文藝評論頻道
近年來,網(wǎng)絡類型小說蓬勃生長,發(fā)展為一股不可小覷的文學勢力。讀了念遠懷人連載于簡書的《三十六騎》,感觸頗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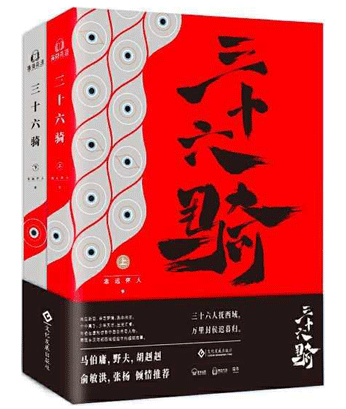
《三十六騎》的故事輪廓依據(jù)于班超使西域的史事。班超奉命持節(jié)西域,開疆拓宇,使西域諸部歸服,這無疑是大漢民族一段飛揚壯麗的歷史。對此,《后漢書》和《資治通鑒》均有記載,可惜只限定于寥寥幾句。在新的語境下,如何在歷史的軀殼內(nèi)改造、變形,如何于史實的有限空間騰挪出諸多炫目的故事?這就很考驗作者的才力了。在《三十六騎》中,作者念遠懷人借助歷史之光,以武俠與玄幻為魔法,締造了一個燦爛的異想世界。
千古文人俠客夢,簫劍平生是中國傳統(tǒng)讀書人從未中斷的迷夢。自司馬遷的《游俠列傳》始,經(jīng)唐傳奇,到民國時期的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再到當代的金庸、古龍,武俠傳奇小說開創(chuàng)了一個快意恩仇的世界。《三十六騎》的核心人物班超身為朝廷命官,經(jīng)常眉眼慵懶、神游物外,“以游俠自命,天性風雅,偏向做些大膽妄為的事情”。后來,他棄筆投戎,為了救兄長班固,勇劫法場,甘作替死鬼。在與班固的辯論中,他更是直抒胸臆,“人總是要死的,與其去談什么高義大德,功業(yè)文章,不如縱情當下,意氣自由。或許只有這自由可以一直流傳下去。”在文章傳世與快意人生之間,班超選擇了與兄長截然有別的道路。
顧頡剛在《武士與文士之蛻化》中曾對“俠”一詞有所考辨,“儒重名譽,俠重意氣”。如此看來,班超這位命官分明是個意氣自由的俠士。班超的胸臆,也未嘗不可視為《三十六騎》作者的夫子自道。念遠懷人因追求縱情意氣的人生,數(shù)十年來憑興趣漂移于繪畫、詩歌、設計等不同領域,不求聞達但求盡興,如今又辭職專門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就為了圓一個少時的武俠夢。同樣,三十六騎中其他成員,都有司馬遷所謂的“重諾輕死”的俠義之風。他們同命同心,一路行來,都在刀口舔血,與一路反派展開殊死搏斗。這一過程中,各類奇兵暗器輪流出場,倏忽而來、飄忽而去,讓人宛然望見古龍筆下的詭秘江湖。
顯然,《三十六騎》更是詭秘的。班昭會望氣,花寡婦會下蠱,柳盆子能潛行術,三十六騎幾乎人人各懷異能。在正反兩方斗法時,巫術、幻術讓人目不暇接。作者以一枝妙筆描繪了西域風光,更把它構建為釋放想象力、制造敘事波瀾的空間。鄯善、車師、莎車、于闐、貴霜諸國仿佛一座座冒險島,怪誕奇異。例如,班超途徑的精絕國為工匠之國,沒有官府沒有軍隊,只講利益;于闐國的神圣城堡由一千人拉動,其中供奉的大巫比國王更尊貴。這類奇幻之國讓人自然聯(lián)想起《鏡花緣》《西游記》中的小人國、獅駝國,以寓言方式影射了現(xiàn)實的生存圖景。念遠懷人的書寫無疑承續(xù)了中國神魔小說傳統(tǒng),吸納了妖術、神仙等民間傳說,并雜取道家仙話、佛教故事的營養(yǎng)。
如果說武玄合流式書寫構建了一個精彩紛呈的想象世界,那么其中漫野生長的知識、靈光一現(xiàn)的哲思則讓《三十六騎》擁有了嚴肅文學的骨骼。念遠懷人自言興趣繁雜,天文地理、諸子百家無所不好。在《三十六騎》中,作者有意編織了一個融儒釋道、奇門遁甲、地理民俗為一體的知識世界,還不時發(fā)揮考據(jù)癖,就上古的某種禮儀乃至每個用詞進行一番追溯。例如,他寫美男子齊歡為“大丈夫”,便就“大丈夫”進行了詞源考辨。作者一旦觸及某個知識節(jié)點,總忍不住談古論今、侃侃而談。有讀者可能認為這是一部逞才之作,不過筆者倒很樂意看里面酣暢淋漓的高論。
《三十六騎》不但展示了廣博的知識面,還呈現(xiàn)了作者朝向諸子百家、釋禪思想進行深度思考的努力。文中塑造的理想人物齊歡可謂墨家思想的具象呈現(xiàn),他摩頂放踵、身體力行,主張非攻等,宛然墨子再世。同樣,棄絕宮廷生活,追求行動人生的班超也可謂半個墨子。在去于闐的路上,代表墨家傳人的齊歡與浮屠教的法蘭就修行與生死,發(fā)生了一段充滿哲思的辯論。法蘭面對齊歡的詰問,這樣來闡釋浮屠的思想,“我們每一個念頭,都是欲望之火,火能生風,推動命運的巨輪,生生世世,轉生無盡,執(zhí)念是火中之火,比如你說的不朽,可能是人們最大的執(zhí)念”。詩性的言說,直指佛家破執(zhí)之說的真諦。
閱讀《三十六騎》,時常會產(chǎn)生一種讀敘事長詩的恍惚感。這不僅因為它始終舒展想象的翅翼,飛翔于庸常現(xiàn)實之上,有著輕盈的體態(tài),還因為它擁有輕靈流麗的語言。風致翩然的詩性語言,構筑了一個奇幻飄忽的傳奇世界。斯坦納認為,世界的極限就是語言的極限,語言所創(chuàng)造的想象力和詩意能讓人類從絕對律令中解放出來,獲得自由。《三十六騎》自由而絢麗的詩性特質(zhì),離不開語言的力量。例如,作者寫班超在父親墳前一夜未眠,見到“東方既白,甚至有點血色。茫茫莽原上,殘碑廢墟比比皆是,焦灰里冒出點點新綠,盡是野花野草。冢常廢,柳常綠,讓班超有無常的感慨。”此類語言文白化合、靈動凝練,廢冢與新柳并置,意象充滿張力,言情布景類似一首宋朝小令。
俗話說,藝無止境。如果問《三十六騎》還有哪些提升空間,個人認為恐怕在于過于輕靈,缺乏朝向人性與心靈維度更深的開掘。當然,這是更高的要求。概言之,念遠懷人儼然有將武俠、歷史與玄幻融為一體的野心,以詩性的語言編織了一個既有歷史支撐,又玄幻詭秘,充滿刀光劍影的武俠世界。作品自由游走于雅俗邊界,為時下飽受爭議的網(wǎng)絡類型小說啟發(fā)了一種新的書寫方向。(楊湯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