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楊爭光 | 文學屬于“過于喧囂的孤獨”
更新時間:2020-06-15 作者:楊爭光 王棘來源:《青年作家》2020年第6期
要了解人,首先要審視自己
王棘:您在讀大學之前,一直是在農村生活嗎?在那個物質與精神都極為匱乏的年代,您的文學啟蒙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您是從什么時候明確意識到想要寫東西并成為一個作家的?
楊爭光:我從出生到21歲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都在老家。小學在村上,四年級到七年級,在一所新建在三個村莊之間的七年制中學。我上的高中距我們村十五里,星期三和星期六回家背一回干糧,其實就是饃,也只有這一個種類。關中平原歷朝歷代都是糧區。在我上學的那個時候,還是缺糧。小麥要首先滿足國家的供購糧,喂養城市,常說的是給人民子弟兵,我們的鋼鐵長城。學生們大多背的是玉米面蒸的饅頭和發糕,用開水泡著吃,就著自制的咸菜。玉米面饅頭很瓷實,泡在開水里不改形狀,也不會亂漂;發糕是經過發酵的面,一泡就化,一攪呢,絕不和開水融為一體。如果是小麥面饅頭,嗯,那是人人向往而不可得的。現在許多人主張吃粗糧,說粗糧比細糧有營養,打死我也不信,也拒絕吃,就像紅蘿卜一樣。紅蘿卜產量高就切條什么什么吃,整個放在蒸籠里蒸熟吃,切成轱轆煮在稀飯里吃,一天三頓天天吃,吃傷了,看見就反胃。有幾年推廣高產高粱,長在地里看著好,可以寫抒情詩,連續吃幾頓就會屙不下,大人給小孩摳屁股是常見的;大人也一樣,不過自摳別人看不見而已。
現在的粗糧可以細做,那時候不行。人并不傻的,沒有各種各樣的調料,咋能好吃?粗糧細做我也不愿吃,是頑固的細糧派。上高中(九年制),我媽想盡一切辦法給我做粗糧細糧混搭的鍋盔饃,現在想來,應該是家里所有的細糧都給我吃了。也養過雞,雞蛋幾乎不吃,要換鹽和醋,想換油沒有,國家管制。到我上大學時,還實行糧票,分地方和全國通用糧票。全國通用糧票是帶油的,地方的沒有。
高中畢業到上大學之前,我在村上當了四年人民公社的社員,對農活很不在行,村人的譏諷嘲弄讓我很自卑,同齡人也不愿和我一起。我媽是哀子不幸惜子不爭。那時候, 書就成了我的朋友。
畢竟是民間,在農村還有遺落的書籍,比如《苦菜花》《迎春花》,連封皮也沒有了,也不知道書名,饑不擇食,有食勝過無食。上大學之后才知道,這樣的閱讀竟都是粗糧!物質與精神匱乏的生命,怎么可能不缺營養?怎么可能有健康的體魄?健康的精神與情感?就這還想當作家,在四年級的時候就想了,就閱讀那些小說。
我和一個同學拉生產隊的蔥轉村賣,掙了十塊錢,去縣城新華書店全買了書,至今還記得,有魯迅的兩本小冊子,還有一本《用階級觀點閱讀<紅樓夢>》,是李希凡先生寫的。怎么也想不到,多年后我竟成為他山東大學的校友。又多年后改編央視九八版《水滸傳》,他是顧問之一,我們在一起討論《水滸傳》。
也能找到細糧。當時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華活頁文選》,選輯的古代文學作品大都是精品,有許多在大學學習中國文學史時又重新學了一遍。《紅樓夢》可以讀,也能買到。我現在還保存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序言是李希凡先生寫的。我買的那本小冊子,很可能是序言的單行本。
高中二年級分班,分在了政治理論班,生吞活剝地閱讀了馬克思的原著。教政治的老師就是我們縣的哲學家了,給我們講《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反杜林論》。那時候全民學哲學,有艾思奇先生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現在回頭看,哲學在那個時代的我們手里,可以那么——那么low。
農村幾年,唯一喜歡的是讀書,拿到什么讀什么。一位收留了我們全家的鄰居有一本小開本豎排版的《唐詩三百首》,看我愛讀書就送給了我,我至今保存著,已沒有了封面和前邊的幾頁。以上所說的,幾乎就是我全部的積蓄和貯藏了。我帶著它們,走進了山東大學。
也有寫作的訓練,除了自己在本子上的胡寫亂記,要感謝我們縣文化館和文化館的老師。回到農村,修水庫是最有個人時間的封閉式勞動,在外地不回家,勞動回來就是自己的時間,遇到雨天,時間就全是自己的。我喜歡秦腔戲,大隊有宣傳隊,每到快過年時會排戲和文藝節目,聽朋友說文化館辦戲曲創作學習班,我就寫了一個獨幕戲劇本,朋友拿給館長,竟被選中,從此一年一度文化館的創作學習班我都能參加,繪畫、詩歌、戲曲還有講故事。文化館的老師各有專業,讓我大開眼界。經他們介紹也看了一些書,柳青的《創業史》第一部,就是那個時候看的。它也許是陜西幾代作家作品里,對陜西作家最具影響力的作品。
王棘:海明威曾說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搖籃,您的童年以及少年時期的經歷對您后來的文學創作有何影響?您的性格受父親或母親的影響大嗎?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楊爭光:我的童年并非不幸,而是貧乏。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貧乏。上大學已經21歲,對世界對事物的認知力可能比同村同年齡的好一些,但所得的也是別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童年少年長身體和長精神都很重要,如果身體沒有什么大麻煩,精神的成長對一生更為重要,尤其是滋養品。
上大學以至于到現在,除了吸收,要把童年少年時吃進去的有毒東西吐出來,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比吸收難多了。這是幾代人的不幸,當然也許別人不這么認為。
如果說有具體的不幸,是因為父親的變故。他上過四年級,是國家公職人員,吃商品糧的。在我上高中的時候,我父親成了勞改犯,我們家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一落千丈。我媽帶四個孩子,要吃要穿,要對付的是日子,而顧不到年月,賣掉了家里所有能賣的東西,最困難的時候寫封信,八分錢的郵票錢,滿村借不到。父親當年的朋友幾乎都不見人影了,親戚也換了另眼,何況村人。在跌落之后,世態和人情會清晰很多。如果說童年少年時代對我寫作有影響的話,應該是對人的觀察。
我很自信我對農民的了解。我對黏稠到拉不開的村社文化有著深深的厭惡,它經常以人情和世故做面紗,溫情甚至關心的背后和深處,都豎著尖刀。許多人很懷念中國的鄉紳階層,在我看來,這只是更壞之后對次壞的懷念,而我們需要的是脫胎換骨的人性。先不說別的,哪一個鄉規民約沒有對健康的人情與人性構成威脅和侵犯?這樣的規約里是長不出人的現代性的。我讀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很好的書,也沒有改變我的看法和觀點。
我的父親死于47歲,在我上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對我很嚴厲,希望我擁有人應該有的所有美德,還要有足夠的聰明。他曾拿著切菜刀追我,在街道上跑了幾個來回,最后他踏進了我奶奶的門。有奶奶,他不敢打我,就改為讓我學習毛主席語錄了。
我母親一直是我們家的主心骨,她要強、倔強,為子女會做到奮不顧身,甚至不顧性命。直到我參加工作之后,她才逐漸退出了勞動者的生活,很不情愿地成了一個悠閑的老人。她去年11月20日去世。她的去世沒有一點征兆。她知道那天我要回去,和我小妹、弟媳還有說笑,去了一趟廁所,突然就去世了。我晚了四個小時。她沒有連累任何人。有朋友希望我寫寫她,我會寫的,在我能寫的時候。
父母的性格對我都有遺傳,更多的則是母親。要說他們對我后來的寫作有影響,是因為他們都是我觀察的對象。
我一直固執地認為,要了解人,首先審視自己,然后是最親近最愛的人。了解了這些也就理解了人的大半。人都有偏向自己的本能,如果對自己和親人不留情面,就會發現幽深處許多尋常看不見的東西。生活是生活,觀察和琢磨是另一回事。人是極其具體的生命,也是所有生命中唯一具有形而上意味的生命。沒有對人的琢磨,說解剖也行,不但難以寫出日常的人,更無法寫出各種非常態情景的人。沒有人,小說還能剩下什么?
王棘:您最初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后來又先后在天津、深圳等大城市定居,但我注意到,在您的作品中,大部分還是寫鄉村里的人,很少寫到城市,您個人認為在農村與城市哪種生活對您寫作方面的滋養更多一些?您覺得如今的鄉村與您曾經生活的鄉村相比,發生的最大改變是什么?
楊爭光:滋養和滋養是不一樣的。如果沒有童年和少年的鄉村生活,我的寫作就不會是現在的風貌和樣態。如果沒有上大學以及后來的深圳,我童年少年的鄉村經驗,在我的作品中就會是另一個模樣。大學以及到天津,到西安再到深圳,使我的目光有了不同的焦距,視野的版圖不再單一。生我養我的鄉村是生命的出發地,不同的城市,尤其深圳,是生命的再造之地。出發地更多的是自然、是情感,再造地更多的是認知、是精神。我每年都會在老家待一段時間。因為朋友的傾情相待,我有好多作品是在老家完成的。
常回老家,也因為母親。我住縣城,她住鄉下,見面不多,對她對我都有一種踏實感。在深圳,相距三千多里,她會擔心我;回到老家,即使生病她也踏實。去年她去世了,老家對我來說就立刻空洞了許多。從她去世到現在,近半年了,我一直在老家,在她的跟前,沒有離開。
但總要離開的,離開之后還會不會像從前一樣,我不知道。母親在,我就不會長大,母親走了,我一夜之間成了年過花甲的老人。
鄉村正在荒蕪,和人心一樣,但對我來說,哪怕只是一片荒草,也是我的老家,是一生的。
人可以不寫作,卻不可以沒有詩性
王棘:您最初的寫作是從詩歌開始的,后來又去寫小說和劇本,您是如何看待這三種文學體裁的?您如何理解詩歌與生活以及生命關系的?請您談一下詩歌對您的影響。
楊爭光:我對詩有過十多年的迷戀。在上大學的前兩年幾乎閱讀了學校圖書館能找到的所有詩集,包括漢譯詩。那時幾乎每天寫一首詩,回頭看,大部分很幼稚。詩的閱讀和寫作有效強化了我的表達訓練,對詩性的認知,拓寬了我對文學和藝術審美的視閾。這兩樣,尤其后一樣,使我終身受益。
人可以不寫作,卻不可以沒有詩性。詩性并非詩的專屬。一部小說,哪怕是一篇短文,有詩性和沒有詩性是不一樣的。詩性不僅是情境交融,不僅是抒情。對我來說,它更多意味著張力和彈性。詩性是豐富的、多樣態的,干枯也有它的詩性,干枯不是干癟,如此等等吧。白話詩、現在的口語詩,如果有借鑒的話,更多的不是來自唐詩宋詞,而是小說、散文、繪畫。經典小說的敘述都有詩性,許多敘述分行排列,就是非常好的白話詩口語詩。
我們說傳神,大多指的是敘事狀物的精確和生動,我更傾向于傳達的神性,有神性的表達,或表達神性。
人是居于神魔之間的一種生命,拘泥于人性的文學無異于報道和新聞調查,不管它有多么離奇夢幻。在人性里發現神性和魔性,才可能與文學發生關系。
詩性也不是寫作人的專屬,更在于生活著的生命。沒有詩性的生活是少有彈性和張力的,有詩性的生命也有神性。也只有這樣的生命,才有我們所說的審美,從人的桎梏品嘗到幸福的滋味。所以,詩性對每一個不甘于日常的人都有效,發現詩性,擁有詩性,是寫作者的,更是每一個人的。
寫小說和電影,我依然看重詩性。有人說我的小說土得掉渣,卻不顯土,洋氣。如果是真的,我就會認為是得益于寫詩的訓練和對詩性的不棄。
我已經七八年不寫小說了,小說家沒有小說就失去了說小說的資格。還是有小說作品了再說的好,至少我不會有太多的難堪。
王棘:詩人、小說家、劇作家這三個身份您最看重哪一個?為什么?
楊爭光:都看重,關鍵是寫好。我希望我能多寫小說。卻又是一個任性的人,管不住自己。我有許多想寫而沒寫的小說,放在筆記本里。想小說比寫小說輕松,更讓我興奮。想法只是想法,寫出來才是小說,想法里的小說與小說距離遙遠,甚至在兩個世界。但愿我能把想法世界里的小說拉到小說的世界里來。
詩比小說單純,寫詩比想寫詩有意思。我1988年之后就沒有寫詩了,過去的兩年里又心血來潮寫了兩百多首詩,學生幫我放在了電腦里。
電影和電視劇都是訂貨性質的。雖然是訂貨,依然對電影心存夢想。希望能寫出既是訂貨又是自己喜歡的電影。去年底,接了一部電視劇和一部電影,正在創作中,希望能有好的結果。
三年前我從抑郁癥里走出來,受朋友慫恿做了一個公眾號。傳統的閱讀與傳播正在遭遇歷史性沖擊,網絡給了寫作更為廣闊的疆域和可能。我也試圖改變一下自己。過去非朋友要求我不寫短文,做公眾號就得寫。對我這樣貪玩懶散任性的人,逼迫是有效的,三年里我寫了幾百篇文章。
我還有意識,也專門花時間梳理了一下中國四十年來的詩創作和中篇小說,各編選了一套叢書,雖然說好的出版因故擱淺,對我卻不完全是白費工夫。我對四十多年來的詩和小說有了我個人化的梳理,也有許多新的發現。我還有意識回顧了中國百年來的散文,也有編叢書的企圖。中國是一個文章大國,白話文百年來創作了多少文章?又有多少是有價值的?
我因為寫作《少年張沖六章》,認真閱讀過從小學到高中的語文課本和政治課本。我們的孩子接受的語文教育比我那時好多了,但不能止步于縱向比較,更要有橫向比較。在隧洞里行走很容易感受到進步,因為堵住了橫向的視角。橫向看,我們的文章大面積同質化,少有思想,少有發現。在隧洞里思考世界、思考人,會有多少發現?而這些,即使選出其中優秀的給我們的孩子,又能有多好的營養?
對文章的梳理和對生活的梳理一樣,悲哀多于興奮。
文章大國并不意味著文章強國,我們需要有真品質的文章。寫公眾號,就是希望自己能寫出些有價值的文章。許多朋友批評我,勸我寫小說,這也符合我的愿望,可我偏偏又是個多愿望的人,還給自己找了一個理由:魯迅說短文章該寫還是要寫的。事實上,如果沒有他的短文章,魯迅作為一個文學存在就會大打折扣。他的短文章實在也是他的小說的互文。
“研究文章的歷史或理論,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的文人,此刻所謂創作家。”這是魯迅的話。他把詩、戲曲、小說拉在一起了,并沒有文體偏見。
好像成工作匯報了,離題了。
小說和影視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形式
王棘:您是老版《水滸傳》的編劇之一,您是否記得您是什么時候開始讀《水滸傳》這部偉大作品的?后來是何種契機使得您參與電視劇《水滸傳》編劇?《水滸傳》這本書對您后來的寫作有影響嗎?
楊爭光:四大名著,我最喜歡的只有《紅樓夢》。在改編《水滸傳》之前,我沒有完整地讀過它。完整認真地閱讀是在接受改編之后。完整認真地閱讀,依然沒能讓我改變看法。中國文學史留給我們豐厚的遺產,主要是文質皆備的文章與詩賦,尤其是詩詞。以抒情詩論、唐詩宋詞,是可與世界任何民族的抒情媲美,有過之而無不及。春秋戰國時的文章,與幾乎同時的古希臘相較也不遜色。我們的先人對世界對人的觀察思考與認知,甚至更老到一些。
留給我們的敘事文學卻蒼白又寒磣,一部《史記》,一部《紅樓夢》,竟相隔幾百年。分別在兩頭,耀眼而孤獨。
《水滸傳》這樣的小說,列入文學經典,有湊數之嫌,從結構、人物到語言,經過多人之手,依然近于一部虎頭蛇尾的著作,70回之后不忍淬(卒)讀,但愿我沒有觸怒《水滸》粉,也許我是錯的。因為有這樣的偏見,也懾于名著改編多陷阱,我兩次拒絕了邀請。制片人卻很固執,決意要我參加。閱讀、分析、梳理,不為自己的喜好左右,確定了改編原則,專門組成了一個編劇組,我擔任組長。二稿過后只有我一人了。我沒寫過這么長的東西。我和冉平完成了劇本改編。一年多的辛苦沒有打水漂。那時候的影視行業沒有現在這么浮躁,從導演到每一個部門,都很敬業,只為作品。又經過一年多兩年,文字成了影像,播出后反響空前,竟成了幾十年間的電視劇經典。說經典,也是和我們自己比,放在世界電視劇的格局可以忽略不計。盡管如此,我還是愿意為它說好話。在我們幾十年的電視劇作品中,它堪稱上品。
能有這樣的結果,編劇是盡了力的,和寫小說一樣,希望能做到最好。對原著有許多改編,竟然能騙過大多數觀眾。《水滸》迷們也欣然接受。比如林沖上梁山之后,再沒有風雪山神廟、火燒草料場那樣的精彩。他的死也只有一句:“病死正將一員,林沖。”這么重要的人物竟如此草率。電視劇里宋江招安捉高俅,唯獨瞞著林沖。等林沖知道,和魯智深策馬趕到水邊,高俅已被宋江禮送遠去。林沖氣極,口吐鮮血而死,魯智深掄起禪杖掄倒了一匹戰馬。有中學生看到此處放聲大哭,也是改編成功的一個證明。
《水滸傳》是我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次改編,也要感謝當時《水滸傳》改編小組領導者的開明,諸多顧問的學養和胸懷,劇組所有人的智慧和付出,拍攝完全忠實于劇本。香港袁家班的武打設計也很給力,趙季平的作曲好,劉歡唱得好。影視是團隊藝術,成功的影視劇是整個劇組所有參與者的成功。作為編劇,我更欣慰的是電視劇沒有腰斬整本原著。我們也強化了后幾十回的人物塑造與情節建構,呈現了招安的過程和結局,方臘一方不再是原著中妖魔化的人物,忠和義的沖突,忠對義的和合,等等吧。
如果不客氣的話,就可以說,央視九八版《水滸傳》是原著成功的文本轉換,是對原著有提升的普及。經過改編強化的宋江,也因為李雪健出色的表演,成為中國電視劇忠和義、忠君愛國的標志性形象。
這部劇的改編沒有對我后來的寫作有大的影響。它強迫我對這部文學名著以及諸多人物進行梳理,也培育了我對它的感情,不再那么偏激。
王棘:您編劇的《雙旗鎮刀客》被影評人稱為中國最好的武俠片、西部片之一,好像《黑風景》最初也是先寫成的劇本,后又根據劇本改成了小說,從劇本改成小說與從小說改編成劇本有哪些不同?對您來說寫劇本與寫小說哪個更容易一些?
楊爭光:《雙旗鎮刀客》是我拍成電影的第一個劇本,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部西部傳奇,里邊沒有俠,有一個自稱大游俠的還是個騙子。它寫的不是江湖恩怨,已沒有自覺的除暴安良。這部電影是慢熱,現在還有人記得它、喜歡它。
把小說改成劇本,或把劇本改成小說,我都有實踐。改劇本為小說是因為不讓拍,我覺得可惜才改寫的。我有過好幾部這樣的作品。《雙旗鎮刀客》拍了就沒有改寫成小說的必要。
我的體會是,小說改劇本容易一些,劇本改小說難。小說《流放》也是從劇本改的,竟改了一年。發在《收獲》之后又拍成電影了。
文字的畫面感和影視的鏡頭是不一樣的,文字的畫面有想象的加持,影視的鏡頭要的是具體和真切,需要表意得飽滿。對小說來說,敘述也許是必須的,對劇本則是多余。小說不能是一個又一個畫面的組接吧?短小說也許可以,長一點就有可能別扭。
王棘:您在寫小說時會不會刻意寫得更有畫面感,以方便日后的影視化?有不少作家認為長期寫劇本會致使作家的文學語言退化,您有這方面的感覺嗎?
楊爭光:不會。小說和影視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形式,卻都拒絕刻意。也有朋友擔心寫劇本寫壞了手,主要說的是語言。我當然不想把手寫壞。怎么辦呢?盡可能把劇本寫成能夠閱讀的劇本。即使是一個一個的鏡頭,不能止步于寫清楚,還要盡可能有魅力,包括語言。
有價值的寫作應該有充分的準備
王棘:許多大作家寫作時有其獨特的癖好,海明威喜歡站著寫,杜魯門·卡波蒂喜歡躺著,您寫作時有什么癖好嗎?
楊爭光:我喜歡拉上窗簾,哪怕是夏天。不關門,不拉上窗簾,感覺我的世界不完整、不安全,我會心神不寧。
王棘:您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樣的?您相信靈感嗎?寫不出來時會想什么辦法?
楊爭光:想好了再寫。至少,寫什么應該清楚。到寫的時候,就多是技術處理,是怎么表述更好一些、更準確一些,也會有突然涌來的表達興奮。因為是事先沒想到的,也就是我們說的臨場發揮、靈機一動。但有價值的寫作不能寄希望給臨場發揮,應該有充分的準備。相反,好的臨場發揮往往來自于充分的準備,以及對于要寫的東西的自信。也有寫不出的時候,寫不出也會沮喪,和我農村時想把農活干好又干不好時的沮喪一樣。也會懷疑自己,睡一覺第二天就好了。事實上每寫一個東西我都很不自信,怕把它寫壞。
王棘:您在寫作一部作品時會考慮讀者嗎?您如何看待作家與讀者間的關系?
楊爭光:潛意識里還是有讀者的。首先是對自己的忠誠,完成了設想就完成了勞動,讀者會不會喜歡是讀者的事。我不可能了解所有的讀者。我覺得好,總有人會喜歡吧?一味想著讀者,我就沒了。
王棘:您在動筆寫一部作品時會做哪些準備工作?作品產生的過程中尤其是寫長篇時,會有焦慮伴隨嗎?
楊爭光:主要是素材和資料以及對素材的分析、揀選,尤其是長篇。寫作目標也會調整。《從兩個蛋開始》的準備,斷斷續續有七年時間。《少年張沖六章》一年多都是準備工作。焦慮會在未寫將寫時,一開始寫就踏實一些了。有朋友說世界上最長的距離是從所在的地方到寫字桌的距離,我有同感。《從兩個蛋開始》出版到現在,已經近二十年了,還想著將來出版時在附錄里附上什么樣的歷史資料,好像這本書并未完成,還在進行之中。當然也因為我比較看重這本書。這本書正式寫作整整兩年,三十六個相對獨立的短章,構成一個魔方結構。五十年的編年史涉及到五十年幾乎所有的大事件,承載這些的是一個叫符馱的村莊。村莊的同質化在我們這個國家是普遍的,所有的村莊大同小異,面對的都是一樣的事件。日常生活里的政治動物與政治的同構、消解,會顯現出什么樣的人性?這竟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竟然能走過來,還自有樂趣。不管是作為個體的人還是群體的人,構成的是一個實在又荒謬的關系,是人的荒謬、時代的荒謬。又過去了二十年,依然是同樣的人,只是在經歷和過去不同的事件,荒謬在加劇,人性在深陷,以赤裸裸的離奇挑戰小說家的想象、挑戰人的底線。極度貧困的精神需要扭曲的激情平衡,扭曲的激情就是瘋狂,瘋狂的人性,締造互害的社會。也許,《從兩個蛋開始》還會有新的篇章。
王棘:您大學讀的是中文系,現在許多高校都開設了創意寫作課程,您覺得創作是可以教嗎?
楊爭光:文學創作就是創意寫作的一種。無創意即無有價值的寫作。
大學的創意寫作課發生于上世紀,美國愛荷華大學經過諸多努力,率先開了這一門課程。其所以要開這門課程,就是認為創作是可以教授的。我們的大學,尤其文科大學也有創作課。對創意的特別強調則來自于創意寫作。
創意寫作作為一門課程,也不僅限于文學創作。各種各樣的寫作,哪怕是廣告文案、尋人啟事,強調創意和不強調創意是不同的。以我的理解,一般的寫作課重視的是寫作的基礎訓練,創意寫作是一般寫作課的升級。尋人啟事重在實用,不強調創意,做到清楚明白即可,強調創意,就可能在確保實用的基礎上,把它寫成有文采有趣味的文章。
影視劇的主創,如導演、攝影、美術、主演等,在過去是要寫闡述的。我看過張藝謀《紅高粱》的導演闡述,就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在保證工作實用之外也具有審美價值。這也是我試圖以文章的視野審視百年來白話散文的原因之一。
我們研究散文文學,經常的情形是著眼于作家和非作家的像散文的文章,忽略了實用性的散文。胡適、錢穆、錢鍾書最好的文章并非他們學術之外的閑文,而是他們的學術文章。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是社會學專著。我們把它當成學術專著,而拒之于文學之外,這是對文學的窄化和矮化。事實上,《鄉土中國》的每一章都是相對獨立、不缺干貨也不失文采的散文。
順便也說說散文的“形散神不散”。這種說法很流行,成為散文文體特性的經典概括。在我看來它是錯誤的。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樣好東西是形散神不散的,形散神不散的東西一定不是什么好東西,不合乎美的規律,不合乎美的規則,形散神不散的文章也一定不是什么好文章。“形散神不散”一說,把文章分成了神與形兩塊,正如內容與形式的分離一樣。如果得過病,就更能深刻地感受到人的靈與肉是一個無法分離的整體。神散則形散,靈在則體聚。如果真有形神之分,寫作領域的形式主義主張,形式就是內容,就會失去存在的合法性。
學術家的學術文章可以是好的文章,是大美文,就在于它的神形一體。
創意寫作也包括學術寫作,應用文章的寫作。創意寫作在強調創意的同時,也強調寫作過程中的心理、思維等問題,交流與碰撞,也被實踐證明是跨越心理障礙、思維障礙、認知屏障的有效途徑,也證明創作是可以教授的。師傅領進門,修行在自己。能不能成為創作的高手和大師,最終決定于自己的造化,這和所有創造性勞動并沒有本質的區別。
關于創意寫作,我曾有過一次訪談,這里不贅述。現在這門課已在很多大學開設了。和文學創作比,各行各業都需要創意寫作的訓練,需要創意寫作的高手。我去年也應朋友的邀約,在哈工大深圳分校以電影劇作為例,講過一學期的創意寫作。
去年,我的工作室搞了一期編劇培訓,一期“城市創意寫作營”,都采用改稿會和工作坊結合的方式。業內作家和批評家大課講授,小組討論交流,指導老師一對一指導。編劇班三十位學員,來自全國,創作的三十部影視劇已入工作室劇本庫,一部已經拍攝。第一批推薦的劇本有三部,已有拍攝計劃,如果不是疫情影響,應該已經完成拍攝。城市創意寫作營的二十位學員均為深圳青年作家,參加寫作營的作品已陸續在《十月》《鐘山》《中國作家》等大刊發表。
寫作也是可以教授的,如果教授的含義不那么狹窄。我們的教育大灌輸,而灌輸恰恰是最初級、最機械的教育。好的教育,是對判斷力和創造力的培養,是交流,是爭論,是激發,是推開門窗。
小說家既是他自己,又是每一個人物
王棘:在閱讀您的作品時,我發現在您的作品中常常看到兩個角色間的“角力”,這樣的對峙除了表現人物性格及內心外,也使得小說氛圍有種緊張感,您覺得這樣的寫法最難把握的地方是什么?
楊爭光:我喜歡寫角力和較量。兩個人,兩個群體較勁和角力本身就有一種張力。膠著的較勁,張力之間有一種平衡,角力的各方都盡力摧毀平衡,張力和平衡就形成緊張關系、一個動態結構。自己和自己較勁也是一樣的。平衡的坍塌就是毀滅。沒有勝利者,有的是激情、是毀滅、是荒謬,沒有悲壯。角力和較勁者也有對話,對話也是角力和較勁的有機構成。我要小心注意的是,較勁不是抬杠,更不是插科打諢。
王棘:您的作品里有很多對話,我感覺您也很擅長寫對話,寫小說的都知道對話是很難寫的,您覺得怎樣才能寫好對話?需要注意什么?
楊爭光:敘述語言是小說家的,對話是人物的。小說家既是他自己,又是每一個人物。對話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也許還是最直接的手段。如果能準確把握人物在事件、情節、具體場景中的心理狀態和情感狀態,他或她會說什么樣的話就好把握一些,容易找到他們應該有的語言。我希望我能把握好每一個人物,包括哪怕只出現一次的人物,盡可能讓他們準確地表達自己。哪怕是一句語焉不詳的反應,哪怕是一個沒有字面意思的語氣詞。也希望在對話中寫出節奏。對話也可以敘事的,也可以推動情節向前或者拐彎的。
王棘:在《驢隊來到奉先畤》中,九娃說了一句話:“世上的事無奇不有。世上的事都是人做出來的。”您在寫作過程中是站在什么樣的立場?您如何理解人以及人性?
楊爭光:我希望盡可能站到局外,對所有的人物秉持同樣的態度,讓他們在事件中作為,把所有的理由都給人物,保留或者疏 漏一個理由,人物的作為就會失去支點,就會牽強。霸王硬上弓是經不起推敲的。作家不能偷懶,不能放過自己,放過自己也就放過了人物。放過人物,作家會一無所有。
人物和故事是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尤其影視界流行“要有好的故事”,“寫好故事”“好看的故事”等等。在我看來,人為之事,為事之人,人和事無法分開,就如同靈與肉一樣。事在人為,說的是人的重要。為事之人,依然說的是人的重要。人是歷史中最活躍的元素,也是事件中最活躍的元素,沒有人就沒有事。無事生非,還是人。老舍說過,戲劇就是湊幾個人物,給他們事情做。他是戲劇大家,說得輕松。事實上很不輕松。合適的人,做適合他的事。魯迅給阿Q 作傳,是先有阿Q 這個人,然后才給他選擇合適的事情。所以,重要的是有價值的人物、值得寫的人物。人物沒有價值,有故事也是廉價的故事。人物乏味,故事就無趣,何況許多小說干脆就摒棄故事,同樣是好小說。
對人和人性的理解不是一句兩句能說清楚的,至少我認為很難說清。人是具體的,人物可以有形而上的意味,或者干脆就是形上的。堂·吉訶德滲透出的人性就具有形上性。這樣的人物和每一個人有關。《靜靜的頓河》里的格里高里是精彩的人物,只和某些人有關。
王棘:我見很多讀者與評論家都說中國男作家的作品中很少有能寫好女性人物的,您認同這種觀點嗎?您在小說中刻畫女性人物時有沒有感到困難?
楊爭光:《紅樓夢》里的女性人物就很精彩啊。這么多精彩的女性,在大觀園里活色生香,是中國小說藝術的一個奇觀。以女性人物論,也許迄今還是中國小說藝術無與倫比的高度。
我更愿意寫男性人物,如果因此說我不擅長寫女性,或者對女性不甚了解,我是接受的,也并不影響我對女性的熱愛。我始終有一個偏見,總認為女人比男人更可靠。我們好色,卻總是忽略女人。女人是我們背叛的對象。什么時候我們像珍重自己一樣珍重女人了,我們的男人性和女人性就會距離健康的人性近一些,就會親近文明。
王棘:在您的小說中寫過許多固執的角色,比如《老旦是一棵樹》中的老旦、《代表》里的代表、《高坎的兒子》中的棒棒,這些角色身上有您自己的影子嗎?有人說作家畢生所寫都是在塑造自己,您是否認同這種說法?
楊爭光:說作家畢生都在塑造自己,包括他寫的小說,并不等同于說作家一生都在寫自己的自傳。作家的作品是作家在他的生活之外建構的另一個世界。這和其他藝術家并無不同,甚至和數學家、物理學家等等,隨便什么樣的家一樣,沒什么特別之處。如果說有特別就是他建構了一個和其他作家大異其趣的小說世界。如果藝術不在現實之外,藝術就會失去它存在的必要,理論一些的說法叫合法性。
我也會固執,卻不如老旦和棒棒,能把一種固執進行到底。能把固執進行到底的就是小說中的人物,和現實世界里也會固執的我隔了一個世界。他們在鏡子里、燭光里,我在塵世。
我從沒想成為一個先鋒作家
王棘:您如何理解有趣?通常什么樣的題材最能讓您產生寫作沖動?
楊爭光:能把固執進行到底的,除了固執之外,更重要的是有趣的。有趣的和可笑的、好玩兒的并不同質,盡管作為旁觀者會覺得也可笑好玩。有趣里有尖銳的東西、殘酷的東西、荒謬的東西,不會好玩一下、可笑一下就完事。有真趣的,好玩一下可笑一下就完事,一定是務實到沒趣的人,這樣的人與藝術無緣。當然,這并不影響他可以是一個收藏家,以藏品致富。一個與藝術無緣,卻終身以收藏藝術品為生命的人,有可能是有趣的,他能把無趣進行到底。一個人很無聊,看一根木棍直直的很討厭,想讓木棍彎曲,這是日常生活里的人。如果因為討厭木棍的直,一輩子為弄彎這一根木棍絞盡腦汁費盡心思耗費體力絕不放棄,就可能是小說。
王棘:您覺得作家該如何平衡作品的趣味性與文學性?
楊爭光:從文學的趣味性或趣味的文學性來說,作品的趣味性也就是它的文學性,不存在平衡的問題。
王棘:八十年代,伴隨著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等外國作家作品翻譯進入中國,引發了一波先鋒文學的熱潮,莫言、馬原、格非等人都在這期間寫出了自己的重要作品,也有人將您的作品歸為先鋒寫作,當年的那一陣探索或實驗的潮流有沒有影響到您的寫作?您如何理解先鋒文學?
楊爭光:我的閱讀總是滯后的,可見,很難有先鋒性。
1986年,我在陜北的一個梢溝里待了整整一年,在那兒的窯洞里,讀了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很喜歡。喜歡他童稚一樣看世界、看歷史、看人的目光。把人的孤獨、群體的孤獨寫得那么熱鬧、那么華麗、那么有趣味。時間和歷史像毛線團一樣團在一起,滲透出的是一種巨大的孤獨,時間的,也是歷史的。
我很早就聽說博爾赫斯了,也看過他的幾個短篇,比如經常被人提起被人稱道的《交叉小徑的花園》,卻沒有什么感覺。一個被稱為給小說家寫小說的大師,我竟對他的作品沒有感覺,這讓我很慚愧,甚至自卑。2005年住到深圳后,博爾赫斯像一個永久的話題,依然有人說。深圳朋友看我一臉茫然,又實在想接近這位偉大的作家,就送了我一套博爾赫斯的作品集。我對博爾赫斯就有了一次認真的閱讀,結果是依然沒有感覺。我也真誠向推崇他的朋友討教過,也看過推崇他的文章,都讓我不知所云。至今,我也沒有走進博爾赫斯。如果非要問我閱讀的感受,我也只能老實回答,他的小說沒有質感。我認為好的小說應該有質感,以中國的文藝理論說,不僅是血肉和骨骼,即使是精氣神,也應該有它的質感。對博爾赫斯的小說,我的感覺也許是錯覺,那就只好承認我的無力,因為無力,無緣這位作家的偉大。
我也曾有意先鋒了一下,寫過幾篇作品。大概是2000年左右,有一篇《爆炸事件》,發在《人民文學》。有一組三篇《我的鄰居》《兩層小樓》和《哀樂與情節》,發在《中外文學》。還有一組三篇更短的,《上吊的蒼蠅和下棋的王八蛋》《謝爾蓋的遺憾》和《高潮》,發在兩個雜志上。其所以分開發,是因為第一家刊物的退稿。這樣的小說并不比《驢隊來到奉先畤》《老旦是一棵樹》更受關注。這也給了我一個偏見,就是,進入現代藝術的小說,在我們這兒很難找到讀者,即使是編小說的資深編輯、大名聲的批評家。哪怕是小說家,又有多少能夠體認小說藝術的現代性?我自己就不能走進博爾赫斯。也很難欣賞卡爾維諾。我看過他的一個三部曲,我喜歡《樹上的男爵》的立意,不喜歡它的表達。
在我們這里,先鋒文學和其他先鋒藝術一樣,大多標簽大于文本。以先鋒自居,很容易被觀念拐帶。昨天的先鋒到今天就可能成為中鋒或后鋒,甚至連鋒也談不上了。對先鋒來說,這實在是很尷尬的。
我從沒想成為一個先鋒作家,也無意于文體實驗,甚至有意識居后一些。我苦惱的是具體這一部這一篇的表達,而不是為所謂的形式和文體的創新。契訶夫是上個世紀和上上個世紀之交的作家,他簡約的表達至今還是極具現代性的,不比后來的海明威差,也不比卡爾維諾落伍。我敬佩所有敢于實驗的開創者,我沒有這樣的勇氣和才力。
王棘:中國人素來信奉“文以載道”,一部分人習慣于把反映社會內容看成是藝術的本質,隨著西方文學的傳播,現代主義文學成為新的潮流,現代主義作家更看重作品的審美感受與體驗,甚至有人提出文學的本質不在思維中,也不在內容中,而是在形式中,藝術的目的不是給人提供認識,而是給人提供感受與體驗。對于這兩種大相徑庭的爭論您是如何看待的?
楊爭光:如果拿幾個公認的現代主義文學文本比較一下,我們流行的、被閱讀者大面積接受的作品,依然是比較老實的現實主義。《白鹿原》和《樹上的男爵》哪一個更能代表我們的潮流?
在我看來,現代和古典的不同,是向英雄的告別、向崇高的告別、向悲劇的告別。在古典小說中,即使是小人物,也有古典美的元素。在現代小說中,即使是大人物也是荒謬的生命存在,或者干脆沒有大小人物之分。在古典小說中,滑稽是諷刺的對象,在現代小說中,滑稽是黑色幽默的素材。在古典小說中,道德和責任即使不是燈塔,也是燭光。在現代小說中是恍惚,是存在的虛無。現代小說中的這些東西,都是現代人對人的發現。沒有這樣的發現,就不會有真正的現代藝術,這應該也是人對自身的感受與體驗,和過去時代人對自身的感受與體驗大相徑庭。古典的人和現代的人,對人和自身都有感受和體驗,處境不同,感受和體驗有了內質的不同。
就寫作而言,我的意見是,寫出真感受、真體驗,管它古典還是現代。如果有爭論,大多是文學家。創作者忠實于自己就可,無需爭論。
如果文學必須走向現代主義,要關注的也許是我們到底有多少現代性?不只是創作者,還有土壤和空氣。以我的觀察和感受,我們現代主義藝術的土壤和空氣還是非常稀薄的。我甚至覺得,還遠未踏入現代社會,我們更多是落后于時間、活在歷史中的族群。
王棘:在閱讀您的作品時,能感覺出您是一位有強烈個人風格的作家,您覺得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您是如何看待風格的?在您寫作過程中會有意塑造自己的風格嗎?
楊爭光:創作者的風格不是預先設計的,而是在創作實踐中自然形成的。托爾斯泰寫了《戰爭與和平》,形成自己的風格沒有?和后來的《安娜卡列尼娜》比較呢?把這兩部和再后來的《復活》再比較呢?是不是要用更抽象的詞來概括?如果托爾斯泰寫《安娜卡列尼娜》時,念念不忘《戰爭與和平》的風格,還能寫出我們看到的這一部《安娜卡列尼娜》嗎?如果寫《復活》又念念不忘《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列尼娜》共有的風格,他的壓力會有多大?能寫出我們看到的這一部《復活》嗎?我覺得還是把風格的問題交給文學家為好,創作者只管關心并盡力寫好每一部作品。只要忠實于自己,總是有一以貫之的東西、相對穩定的東西在每一部作品之中,能讓聰明的讀者看到隱現在每一部作品中那一個獨一無二的作家。這就是作家最鮮明的風格,最大的辨識度。
我不相信寫《從兩個蛋開始》《老旦是一棵樹》和《上吊的蒼蠅和下棋的王八蛋》的不是同一個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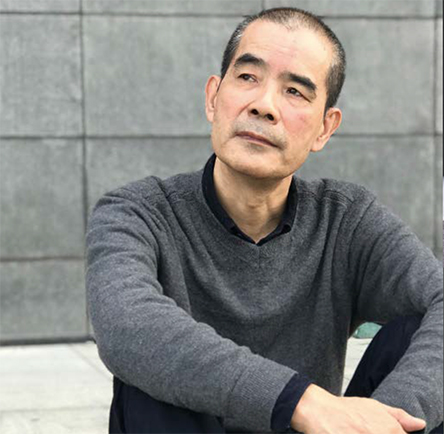
楊爭光, 1957 年生于陜西乾縣;詩人、作家,國家一級編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1982 年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長期從事詩歌、小說、影視劇寫作,作品被翻譯為英文、法文、塞爾維亞文、俄文等外語在世界多國出版發行,其中《老旦是一棵樹》被改編成法語電影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展映,《公羊串門》被改編成話劇在維也納上演;著有《棺材鋪》《驢隊來到奉先畤》《越活越明白》《從兩個蛋開始》《少年張沖六章》等小說,出版有十卷本《楊爭光文集》及多部小說集、散文集、詩集;作品曾獲莊重文文學獎、夏衍電影文學獎、《人民文學》小說獎等;電影《雙旗鎮刀客》編劇,電視連續劇《水滸傳》編劇、《激情燃燒的歲月》總策劃、《我們的八十年代》總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