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王威廉 | 文學的游牧
更新時間:2020-06-12 來源:南方+
放在我面前的這幾本墨綠色的新書,是我的隨筆集《無法游牧的悲傷》。
收在這本書里的隨筆和評論文章,最早可以上溯到十幾年前,所幸的是,那些論述過的書以及自己的觀念,如今看來依然具有價值。盡管這很可能是一種敝帚自珍的作者心態,但我把這些文章從時光的河底打撈、匯聚于此,它們的確給予我了文化的信心。
審視這些思想的腳印,我慶幸自己從未將寫作視為一種完全個人的事情,也從未劃定領域、固步自封,只談論和小說有關的事情,我盡量站在低處,將自身敞開,目睹時代的巨大軀殼如何收縮和伸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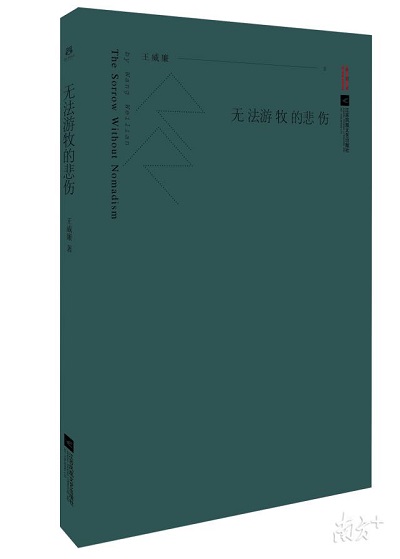
可以說,這本書體現了我的文學關懷。
我珍視同時代人的創作、珍視同時代人的思考、珍視同時代人所經歷和承受的一切:他們的歡樂與疼痛,他們的表達與郁積。并且,我珍視這種珍視的無功利性。
正如書中有一些文章是關于朋友作品的品評,其實這種品評帶有極大的偶然性,因為主觀總是太狹窄了,大多數時候只是按照既有的經驗去選擇,但是忽然間,朋友出現了,這個人和這個作品就這樣不由分說走進了我的視野,照亮了我的眼睛,拓寬了我的生命。
我想,這一定也是同時代人的意義之所在。
有高論者常常提倡“只讀經典”,不讀當代作品,因為當代作品沒有經過時間的淘洗。
那么,試想一下,如果將“只讀經典”作為一種嚴苛的標準,當代人寫的著作統統放棄不讀,我們對于自己的時代豈不是一無所知?對于自己時代的問題也將無從置喙,這個時代又如何產生自身的經典?這難道不是一種可怕的失職嗎?因此,這是多么荒謬的論調!更不必說從來都沒有“時間淘洗”這回事,進行淘洗的還只能是人類自己。
如果說經典作品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高度和尺度,那么我們自己時代生產的作品則提供了我們進行思想的基本視域,我們得辨析我們自身的新經驗和新形象,還得對逼近的未來做出回應。
除了同時代人的藝術,還有同時代人的理性。
那些理性的聲音從許多學科綿綿傳出,從各個方面判斷著時代。那樣的聲音是文學藝術的盟友。我被文學所吸引著走上語言的道路,一方面確乎因為有很強的傾訴欲,似乎非得要把和世界遭遇的點滴分享出來才善罷甘休;另一方面,是對文學所營造的那種氣息的迷戀,人在那樣的氣息中似乎可以擺脫各種力量,變得更加輕盈,即便還有些許笨拙,但也是可愛的笨拙。最重要的是,人帶著那樣的氣息生活似乎會變得更有尊嚴。
那樣的氣息容納著理性的聲音,讓它們共存,讓它們辯難,讓它們最終產生了光芒。但那樣的氣息在日常生活中無疑是隱秘的,是稀薄的,是需要去捕撈、搜集和創造的。于是,我像蜜蜂,也像蜘蛛,到處去探頭采擷,時不時還拉絲結網,不自覺地構筑著自己的思緒空間,在點滴沉淀中就有了這么一間陋室,希望來客進來小坐時,也可以聞到那種氣息的迷人之處。?
但是,究竟何謂“文學”?
至今文學理論家們還在尋找定義,但文學本身一次又一次溢出那些定義畫好的界限。小學生寫的辭不達意的作文,好像離文學很遙遠,但如果放在適當在語言空間中,卻能達到催人淚下的效果。這就是文學的神奇。文學的氣息,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神仙的呼吸,可以點石成金。因此,文學是知識,有自己的脈絡和歷史,但文學最終超越了知識,超越了理性,生成的是一種文化的精神和生命的意志,更新著我們看待世界的目光。
故而文學的姿態不是守成的,而是游牧的,它不斷漫游、跨越、尋覓和眺望。立身其間的人也應該如此。盡管有小說家、詩人、批評家之類的劃分,但應該看清這種社會學面具的局限性,從而專注于寫作本身。這不是意味著那種“跨文體”實驗,那種實驗也許是種誤會,我的意思是我們要從不同的文體寫作中汲取收獲。就像糧食經過不同的加工,可以變成醋,可以變成醬油,也可以變成酒,這幾樣東西都是我們所需要的。
寫作在用特定的文體、具體的文學形式去呈現,但“呈現”的是什么呢?一種與寫作主體的存在相關聯的精神形式?還是超越主體經驗之外被想象力所凝聚而成的事物?也許都有,也許“呈現”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極限的游牧挑戰,要將邊界不斷推向遠方。 ??
提到游牧,自然會想起德勒茲。這位后現代的思想者,為“游牧思想”搭配了兩個關鍵概念,一個是“平滑空間”,一個是“條紋空間”,前者如草原般平滑無際,可以隨意變幻疆域,而后者則充滿了等級、領域與壁壘。無疑,這兩個概念是如此形象,是頂級的隱喻。
而我們也來到了這兩個空間混雜的時代,網絡的“賽博空間”更像是“平滑空間”,日常生活則一直是“條紋空間”的大本營。如今手機已經成為我們隨手攜帶的身體器官,我們既生活在“條紋空間”,又生活在“平滑空間”,但我們似乎并沒有神經錯亂,而是有條不紊地在兩個空間之間切換著。
但是,這兩個空間的精神在融入彼此的同時,一定在改變著對方,而我們終究只能是兩個空間碰撞交織的妥協產品。
定居者體驗到了游牧的樂趣,而游牧者,也許感到了定居者的束縛,也許感到了定居者的踏實。而我認為自己是個天生的游牧者,這或許是命運的安排:
我祖籍西安,卻出生在青海金銀灘草原,那是地道的牧區;祖父以《官箴》中的“公生明、廉生威”給我取名,可“威廉”卻又是西名的中譯;我是西北人,卻在嶺南的溽熱中已住了近二十年,還患上了鼻炎;我自幼立志要做科學家,苦讀理科考入大學物理系,卻決定重新選擇文學作為安身立命的事業;于是夢想進入中文系,卻不得進入,后來輾轉到了人類學系;即便寫作,一開始也是想做詩人,而不是寫小說;還有嗎?星座學家說了,我還是個雙子座,屬于風向……
因此我親近“游牧的思想”,并實踐“文學的游牧”。文學的游牧就是把那些錯位、那些挫折、那些陌生、那些迷茫、那些深夜中的淚水、那些陽光下的歡笑團聚在一起,彼此相連,卻又讓它們各行其是,因而它們像高原牧場一樣生機勃勃。這自然是平滑空間的產物,但是,它們卻要彌散在條紋空間中,讓“條紋”或是“藩籬”顯現,從而逃避、逾越乃至改變。這并非不可能。這是歷史的重鑄,這是歷史的微觀機制,這是歷史形成的真相。
而文學的游牧,依然不會就此駐足。文學會穿越一個又一個空間。而無論是什么空間,那個闊大無邊的世界或宇宙都如其所是,無所謂熱情,也無所謂冷漠。只有寫作是一種來自深處的呼喚,那出自人心的深處也出自宇宙相對應的深處,物質形態的世界開始顫抖,因為這聲呼喚,世界逐漸獲得了自己的臉孔和目光,與人類呼喚的目光得以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