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從語言本體論到人文整體觀——陳培浩文學批評研討會精要
更新時間:2020-03-23 來源:華夏雜志
王威廉:陳培浩是我敬重的青年批評家,他今年成為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他的批評文章總讓我眼前一亮,呼應著一種大的人文整體觀,尤其是他近期出版的批評文集《互文與魔鏡》《穿過詞語的密林》《正典的窄門》顯示了他寬闊的文化視野和精微的批評技藝。可以看到,他已經獲得了一種自覺的批評意識,這是特別難能可貴的。現在許多的文學批評是僵硬的,幾乎成了一種職業化的話語慣性生產,對作品沒有恰切的審美判斷,不僅與作家的藝術世界脫節,也和社會的實用性知識脫節,淪為無效的知識泡沫。有自覺的批評意識,便是能統攝作者、世界、文本這三者,形成對時代的整體性闡述。培浩是有自覺的批評意識的,在他的學院話語里,我們還可以看到頻繁出現的抒情性話語。學院風格跟詩學的結合,正是思想與感性的結合,是知識與激情的結合。他有寬闊的文化視野,不僅僅是說他涉及的文化信息量比較龐雜,而是說他在發現文本的關聯性方面展現出了精神性的寬闊。他以文本的連接性,試圖努力創造出一種人文整體性。有了人文的整體性,有了這樣一個堅固的基石,我們對他的辨析與闡述才能有一種出自心靈的信任。
楊丹丹:陳培浩的文學批評與同代人文學批評相比較,呈現出極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由文學批評的文學史視野、文學批評的社會化和文學批評的個體化三個維度構成。
我重點談論一下,陳培浩文學批評的文學史視野。這里的文學史視野是指陳培浩的文學批評始終在尋找突破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框架的路徑和可能性。從常規意義上而言,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對象往往直接指涉當下文學發生的文學現象、文學作品、文學事件和文學論爭,強調文學批評的當下性和現場感。這種文學批評路徑和方式,一方面可以呈現中國當代文學鮮活的場景,能夠及時捕捉到中國當代文學正在發生的信息,但另一方面對“當下”和“在場”的不斷強化,也使當代文學批評只能展現出中國當代文學的橫截面和側影,不能整體、系統、全面地審視中國當代文學的動態發展流變。針對這種局限和弊端,陳培浩的文學批評選擇把中國當代文學放置在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整體框架內去衡量,從中發現當下文學的起源、發展和演化的整體脈絡,以及當代文學的世界意義,在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上勘察和完善當下文學創作的價值和意義。例如,陳培浩對麥家的新作《人生海海》的解讀,一方面把小說放置在中國諜戰題材和偵探題材小說的整體發展脈絡中去考量,發現《人生海海》的同構性和差異性,另一方面,又把《人生海海》與《紅字》《奧德修紀》等世界文學經典進行比較,從中發現小說的普遍性意義。這樣就使文學批評散發出一種宏觀和闊大的氣象。
文學批評的社會化是指陳培浩的文學批評突破了對文學內在審美闡釋的拘囿,把文學批評的功能和效用指向中國社會中現實發生的重大社會問題,企圖以文學批評為中介和通道,為社會問題尋求解決方案。文學批評的個體化是指陳培浩的文學批評擺脫了單向度的批評知識生產的牢籠,在技術化和理性化的文學批評中注入個體化的情感和溫度,讓文學批評顯得溫潤而淡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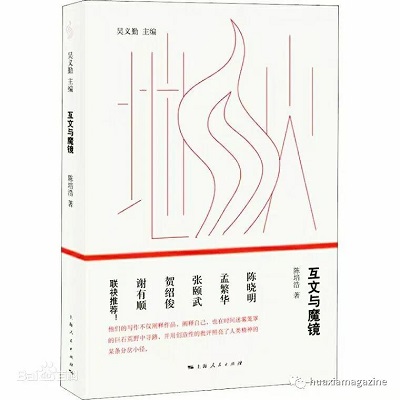
▲《互文與魔鏡》 陳培浩/著
鄭煥釗:20世紀60年代以來,受到索緒爾結構語言學的深刻影響,包括文學理論與批評在內的西方人文學界進行了語言學轉向,從結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對意義表征問題的討論成為人文學科的共同關切點。20世紀末,又發生了文化轉向,但這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以語言表征為基礎,重回人文主義整體觀,對文學批評而言,則是在書寫的符號系統上,去重新接入人類精神的大系統,重回文學與人類之間的整體關切。上一次我們對培浩的討論主要集中于其互文性的批評個性,而從今天這一論題重新閱讀培浩的批評,可以發現,對跨媒介敘事的互文性批評只不過是他尋找文學中所包含的共同人文思考的一種方式,如果從更深入的層面,我們可以看到,培浩其實是將批評作為進入中國現代精神狀況的媒介,比如對艾云散文的閱讀,是作為他對經歷過 1980年代思想啟蒙的一代知識人在世紀末社會轉型以來的精神出路的考察的一種方式,顯示出其批評背后有著更為廣闊的人文思想背景。對楊克詩歌的“民間性”與“人民性”的討論,則是基于一種極為敏銳的問題意識,他看到了“民間性”與“人民性”這兩個概念在中國現代的精神脈絡,及其詩人對于其固有意義的突破。而他對王小波的討論,也是不滿于黃平從自由主義與新左派這一思想史討論框架出發,對其所進行的虛無主義的評價,他正是透過文學經驗的細微剖解,來形成對王小波文學經驗的新判斷。因此,于文學經驗的細微之處,打開當代思想的復雜空間,這就是培浩文學批評的個性與追求。
唐詩人:陳培浩文學批評的問題感,這是非常突出的特征。我想強調的是,陳培浩文學批評關注的問題與很多批評家熱衷的問題不太一樣,他近幾年的批評創作,特別清晰地表現出了對人文總體性問題的思考。比如他擅于把知識譜系的問題轉化為精神譜系問題。就是說,培浩在評論詩歌、電影或者其他文本的時候,關心的問題并非僅僅指向文學史或者知識史、學術史,他不只是為彌補某種知識缺漏而寫作,更多的時候是朝向我們今天的人文精神狀況而展開批評。他熱衷的問題,比如旅行影像背后的精神還鄉問題、知識分子的精神骨氣問題、荒誕話語的精神變異問題,等等,甚至包括分析格非小說《望春風》時論及的一代人的鄉土情結問題,這些問題,都是超越文本本身的一個更大的、牽連著當前社會現實和當下時代精神的問題。在這里,文本細讀和精神思想的判斷和論證,結合得非常好。而且,通過文學批評的方式,把知識譜系上升為精神譜系,實際上是為今天我們的內心狀況尋找一種歷史源流,用語言、概念等知識層面的發展變遷厘清我們今天各種現實遭遇背后的精神流脈。這種批評,幫助我們理解一個作家創作的精神資源,更引導我們去思索一種有歷史感的人文總體性問題。當代作家的精神資源非常繁雜,我們的經驗也是斷裂而破碎的。當代人經常有一種無根無源、無依無靠的失重感和失落感,通過文學閱讀和文學批評來把握和重建我們的時代精神總體性,這或許是今天的作家和批評家們需要特別重視的問題。對此,我以為批評家陳培浩已走在這條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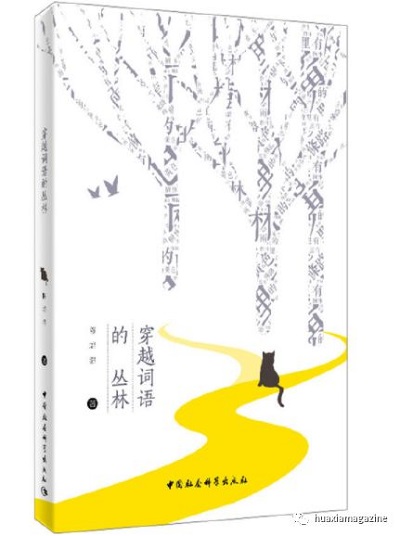
▲《穿越詞語的叢林》 陳培浩/著
馮娜:陳培浩的文學評論給人的總體印象是視野開闊、知識廣博,有縱貫古今中外、縱橫捭闔的氣勢和抱負,或者說你看得到他這樣的努力。正如他《互文與魔鏡》一書的中心詞——“互文”,他在該書中勾連了不同時代的眾多文學藝術形式和它們內在的共振;無論是經典文學還是流行文化,都在他筆下獲得了具有生命意識的對照和重述。從陳培浩關注的作家、文本、社會議題等內容來看,他的知識結構絕不是碎片化的板結的,而是參差對照、有機聯系、自成體系的。“互文”作為一種方法,也是他觀察世界、研讀作品、體察生命的生活邏輯。
此外,陳培浩還是一位問題意識和闡釋能力都很強的評論家。他曾在早期關于詩人朵漁的一次討論中提出了“詩人獨特的職業道德究竟是什么?我以為是語言的想象力、生命困境的發現和精神承擔的自覺”。我想這也是他所認可的、立足于文學批評的“職業道德”的一些基本點:語言、生命困境、精神承擔。譬如他在談論《蔣公的面子》、李安的電影、《云中記》等作品時,你能看到他對世事的洞悉和覺察,也有對創作者本身的體恤和理解;他不僅看見了它們,也“照亮”了它們。
我覺得他的近作《正典的窄門》書名很有意思,在這個正在失去象征意義的世界,一個重視“隱喻”的批評家,怎樣面對“窄門”本身也是一個問題。我想這也是一個創作者了不起的地方,他理解無限之中的有限,正是這種“窄門”和有限,讓我們試圖去具備“大象穿過針眼”的技藝。我想陳培浩不斷提出創作者共同面臨問題的文學批評是接近一種讀者理想的范式;作為一個創作者,我期待從他的批評中得到更多的啟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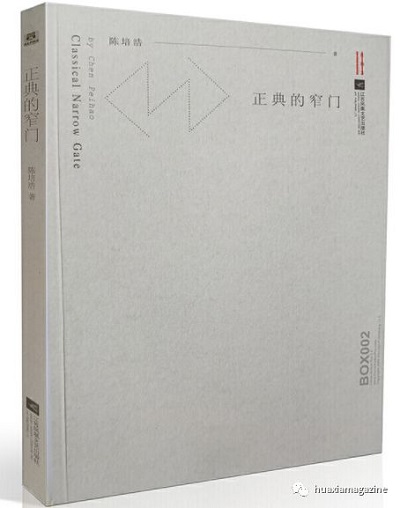
▲《正典的窄門》 陳培浩/著
陳崇正:閱讀陳培浩的評論集,從《迷舟擺渡》到《穿越詞語的叢林》,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評論家的成長性。首先,應該看到這種成長性背后,最為重要的一點是陳培浩的理論建構背后有一個很好的詩學背景。他寫詩歌,同時也研究詩歌,有一條詩歌的路經一直在影響著他的研究和創作,讓他與其他的評論家形成差異,關于如何看待世界,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也因為詩歌,讓他的評論多了一份親切,這種親切區分了詩與非詩,讓他在切入文本時多了一種通達的可能性。其次,我們應該看到陳培浩作為一個在國內嶄露頭角的評論家,他的成長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難。他與我一樣都來自潮州,潮州是個小地方,我們都需要克服重重困難,從窄門走向世界,完全依靠才華劈山斬石,打出一條路來。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有條不紊地建構了自己的體系,立足嶺南,放眼全國,既能看到本土作家的成長,又能夠看到經典文學生成的路徑。而不像一些評論家那樣功利,專門挑大咖寫論文,因為容易發表。最后,陳培浩的評論有自己的節奏,他扎扎實實從文本細讀,慢慢走向人文整體觀。陳培浩的評論具有比較文學背景,所以不會拘泥于一處,而會一直保持一個很好的視野,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尋找可以勾連打通的命門。他總是能非常敏銳地捕捉到文本細部的共通性,并進行準確的命名。如果讓我也給他的這樣一種能力進行命名的話,我會說這是一種非常強大的“提取術”,他能夠在文本中很準確地提取出可以攻擊的目標,或者應該表揚的地方;他能夠很快捕捉到敵人,以及可以把酒言歡的朋友。正是這樣的能力,讓他的評論從經驗走向審美,在剖析中見溫情。
陳培浩:感謝各位的研讀、謬贊和鼓勵,其中很多我尚未抵達,比如以互文性為方法、對文學形式本體的體貼入微,但又使其具有歷史的品格,這確實是我自覺追求的方向。我要提到詹明信的一句話,大意說批評要從文學形式出發,并在更高的層面與政治相遇,這里的政治當然是宏觀的文化政治。很多批評家并不具有對審美形式的敏感,他們掄起理論的大刀,將文本大卸四塊,文本在血肉模糊中呻吟。另有很多批評家,他們不無對文本的敬意,但他們似乎又能入而不能出,能夠敏感于文本的肌理和褶皺,又有足夠大的視野從細微的形式潮汐中透視到歷史和政治之波瀾壯闊者,實在并不很多。這便是所謂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陳培浩:文學博士,副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簽約評論家、潮州市作家協會主席。
我想提到一個概念,叫批評的呼吸。會呼吸的批評,面對的是生命的困惑、難題和激情,所以批評不是作為學科知識的慣性運動和推衍,后者是知識體制化之后的產物,我們為什么需要文學批評,就是因為在知識體制的縫隙,生命有那么多的問題和困惑需要去指認、發現、命名和發聲。與生命沒有關聯的,是不能呼吸的死知識;而我夢想的,卻是能呼吸的批評。
批評為什么會呼吸,還關涉著另一個問題,批評的空氣是什么?在我看來,在今天的后現代知識語境中,人文整體觀依然是批評的空氣,在一個破碎化的時代,假如我們對于人文的完整性沒有一種信仰,我們的批評恐怕很容易窒息為死硬的知識。但是在一個文學的小環境中,志同道合的朋友們相互的砥礪問道,比如今天這樣的小型而有效的研讀會,也構成了批評的重要氧分。因此,我想說:讓我們互為空氣!讓風吹過,石頭開始它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