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陳崇正: 以先鋒精神講述南方寓言
更新時間:2019-01-23 來源:廣東文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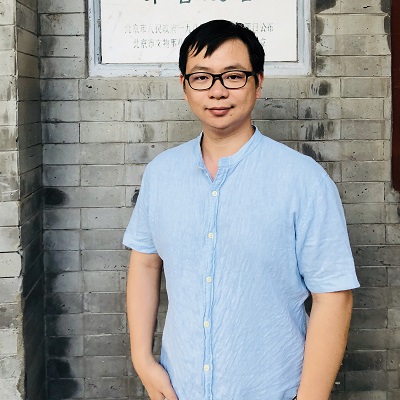
作家簡介:陳崇正,1983年生于廣東潮州,著有《折疊術》《黑鏡分身術》《半步村敘事》《我的恐懼是一只黑鳥》《正解:從寫作文到寫作》等多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017年入讀北師大與魯院聯辦碩士班;現供職于花城出版社《花城》編輯部,兼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創意寫作專業導師、韓山師范學院詩歌創研中心副研究員。
訪談:
魔幻里的現實主義呈現者
?□陳崇正 ? □《文學報》何晶 ? ?
“文學地理”和“魔幻現實”,是解讀青年作家陳崇正小說的兩個關鍵詞——故事總發生在半步村,在這個相對集中的時空里,人物被不斷喚醒,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也不斷喚醒陳崇正對于歷史、時代、當下的感觸,并雜糅了魔幻現實、民間傳奇的敘事方式。
“世界正在劇烈的顛簸中失去形式,而陳崇正力圖創造一種似乎源于薩滿或精靈的幻術,使不可能的看似可能,使不可理解的得到講述。”評論家李敬澤如此評價了這位“80后”寫作者。奇詭的想象力、變異的現實鏡像,是陳崇正尋求小說接通現實的方式。因而他的小說都有復雜的情節和結實的密度——分身術、離魂術、巫術穿行其間,同時裝置著鄉村與城市現代化進程的種種現實映照,正如他所說,“小說如蜘蛛網一樣布滿生命的脈絡,每一個絲線的顫動,都可以被感知”。
記者:你的小說總發生在一個地方——半步村,有人稱其為你的“文學地理”,在其中建立了一個言說與承載多種內容的空間。你曾說這樣“既省事又能成系統”,但多次重復構建這個村莊橫截面和縱向歷史,應該有更多的考量。
陳崇正: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敘事原點。碰巧,我的敘事原點就是半步村。這個虛構的村莊在不經意間出現在我的筆下,讓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諧音“半不存”的村落帶有某種南方的寓言。如果不是半步村,也一定有另一個載體需要被用來承載我的想法和情緒。我多次試圖用一大張白紙來描出半步村的地圖,以期在小說中對村中各處的描述能更為嚴絲合縫,但我發現這樣做非常有難度。最大的難度在于,半步村并非一個村莊,而是由兩個三個甚至更多的村莊組成,我當然可以將之具體畫出來,像很多作家所做的那樣,給出一種秩序。然而我似乎更愿意讓它具備一種混沌的美感,讓它有云霧繚繞,讓它有各種模糊的邊界,讓它陌生而又自相矛盾。
當有人問我寫什么類型的小說時,我通常不知道如何應對。因為我大概只能說我不是寫類型小說的,但具體是哪種類型,真的答不上來。但有一兩回,旁邊另外的朋友會幫我回答,他是寫鄉土文學的。很簡單,你不是寫半步村嗎?當然是鄉土小說了,久之我為了避免各種麻煩,也會直接答曰鄉土小說。然而在我看來,當下的中國已然城鄉莫辨了,農村城市化,城市也在農村化,哪里有真正的鄉村了?怎么樣才算是真正的鄉村?已經沒有概念了。所以說,要去理解城市中的種種焦慮,要去深思這個時代的痛點和尷尬,切入點不在城市,不在工廠,不在流水線,不在咖啡廳,而在四不像的農村,在異化之后無法言說的農村。這個農村不是莫言的農村,也不是沈從文的農村,而是由推土機和遠方沒有鄉愁的人們組成。
所以,如果說我在其中裝入什么,那我什么都裝不進去。畢竟作家并非思想家,作家應該做的事是去發現和呈現。即使如魯迅那么聰明的作家,他面對凋零的故土,他的路數也是有選擇的呈現。這種呈現本身就帶有某種想法和情緒。是的,我反復強調這里面的情緒,只因為我在拆解和拼接中感受到了心頭琴弦的顫動,那是一種百無聊賴的情緒,來自陌生的當下,也來自遙遠而值得緬懷與反思的過去。
記者:你的半步村是一個集合了魔幻、民間傳奇、現實鏡像的敘述空間,分身術、離魂術,甚至巫術、神秘力量都被你拉來使用,魔幻逐漸成為你小說的一個有力武器,其實你的小說并不是一開始就魔幻的,但這種夾雜著通俗小說敘述的先鋒“魔幻”或者說“魔幻現實”確實成為你小說的重要風格。它們讓你找到了最合適的表達了嗎?
陳崇正:這幾年的創作,我似乎非常自覺地將自己的筆觸分為兩類,一類是相對寫實的,這在《半步村敘事》中得到表現;另一類,則更為奇思妙想。對我而言,小說的難度考驗上,如果無法深刻,那么也無妨讓筆下的世界更加有趣。就如我讓“破爺”一次次走進半步村,這個不存在的人物,和不存在的魂機一樣,代表了詩意對破碎的一次次進軍,分身術不過是堂吉訶德的長矛在空中舉著。我也不知道這樣的姿勢能表達什么,或者說,我只是遵從了內心的某一種自覺:應該如此,于是便如此。從技術上考量,這樣的“奇技淫巧”其實也沒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在炫技方面,有太多的人做得比我好。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對分身術等技術設定的組裝方式:根在嶺南,根在潮汕平原,但折射和吸收的,其實是我一次次旅途所見,一次次走街串巷,那些難得的采集。比如《黑鏡分身術》中有個女孩叫譚琳,其原型就是我某次一個人到湘西鳳凰旅行遇到的一個姑娘。那天我無意間走進了一家手繪店,店里掛滿了各式的衣服,斑斕的,和還沒有上色的白襯衫。一個女孩蹲在地上低頭擺弄著調色盤。這女孩就姓譚,我坐在店里跟她聊了兩個多小時,這個白紙一樣的姑娘,長得漂亮,但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讀完中專,學會手繪,然后就開了這樣一家店。我是第一個愿意坐在雜亂的店里跟她聊天的旅客,我們加了微信,然后其實就沒有再聯系了。一直到有一天,我發現她在朋友圈里開始發一些酒吧的照片,以及一些在深夜騎行中認識的朋友,便知道她的生活正在悄然發生改變。她此后的生活,便是這個小說中另外人物的原型,比如她自己的分身,比如另一個奔放的姑娘關滿。我想象的觸覺,一直在觀察著這樣類似的人物,然后我悄悄將之組裝到我的半步村世界之中,同時封上了敘事的密碼。
記者:無論是分身術、離魂術還是別的什么,其實對應的是現實里人們真實的生存狀態和處境,荒誕之下是一種現實焦慮,時代大潮碾壓重塑了許多東西——鄉村、情感、人性,可以發覺你對時代、歷史、現實的興趣很深。
陳崇正: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技術正在改變每個人的生活。我常常想,一個生活在1997年的人,該如何想象這個2017年的夏天:摩拜、微信、人工智能和王者榮耀。面對這樣的時代,作家何為?和歷史上所有偉大的時代一樣,這個時代也有它的側面。我想,作為一個作家,應該站在偉大時代的側面,幽微的側面,暗痕遍布的側面。那里有普通生活的全部紋理,那是作家應該在的地方。在時代的側面,有許多普通人經歷過1997年,經歷過“非典”時期,經歷過悄然發生的信息時代。這些時間節點,對于普通人來說,并不具備重大意義。生命對他們來說,是由具體的一個個事件構成的。這么聊過于玄乎,還是舉個例子,比如《葵花分身術》中,有兩個來自中國香港的老人,原型是我在福建土樓圍龍屋里遇到的兩個中國臺灣老人,他們是過來尋祖的。我跟他們有過短暫的攀談,近乎于碎片的一個記憶,只記得那是一個炎熱的下午,山風從圍龍屋的門口吹進來。但那個下午的聊天,居然讓我念念不忘,回響至今。直到我寫這個小說的時候,這兩個老人突然就浮現了,我清楚記得他的布滿口袋的馬甲,他就是從胸口的口袋里掏出眼鏡和記事的小本子的。從他們的角度看過來,我不過是他們尋親之路上的某個路人。而他們對我來說,代表了一類人的共同記憶,夾帶著戰火、饑餓和奔逃的人們。對于一個寫作的人來說,記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東西。那些我們以為會牢牢記住的,總是被淡忘;而某些不經意的情景,會隨著時間而奔突、侵襲、反芻,如同一個焦急的孩子,要你知道它一直都沒有被時間沖走。
記者:最近出版的《黑鏡分身術》一書是一次集中展現,但你卻在序言里說擔心自己走了偏鋒,怕走什么偏鋒?這樣的敘述又會繼續多久?
陳崇正:對我來說,我大概是暫時使用了分身術。我不會長期迷戀某種技術。或者說,我還在不斷地變換著自己。就如《黑鏡分身術》書中的五個故事,它們分別寫于不同的時間,所以也具備各不相同的五種形態,而不是像搭積木一樣的疊加。或者說,我進行的是流動的加法,這是我的游戲。或者這種游戲方式會繼續進行下去,也或者會有新的玩法。在眾相紛紜的龐大世界面前,當作家窮盡想象希望介入現實的時候,他將別無選擇地滑向先鋒。而這種先鋒,便注定是流動的先鋒。所以,先鋒在被定義之前,都會被認為無法遠走的偏鋒。
記者:其實孤獨、恐懼、虛無,你小說里這些元素也有很多,甚至這些東西才是你小說真正的底色,這些可能是你對人的生存感覺的一種認知。
陳崇正:如果人生是一個巨大的游戲,那么,讓我們完美進入沉浸式體驗的,正是孤獨、恐懼、虛無之類的生存底色。能讓我們覺得我們活在時間里,真的是上天的恩賜,也是人之所以成為人而不是動物的基礎。所以,我們的孤獨和恐懼,終將會在時間里被消解,這其中有不可言說的詩意。對小說家而言,慢火燉煮這些終將消解的生存感覺,控制好火候,就可以在其中安插任意的插件,比如分身術,比如折疊術,比如其他的想象模塊。
創作談:
在分身與折疊之間的碧河世界
?□陳崇正
小說集的名字,最容易偷懶的做法就是選取其中的篇名來做書名,所以有了《折疊術》,也是對以前“分身術”系列小說的一種呼應吧。但它本來的書名,應該叫《尋歡》,也就是這里第一篇小說的題目。“尋歡”這兩個字來自我小時候最喜歡的武俠人物李尋歡。小李探花放蕩不羈而又用情至深,武功深不可測卻有一身壞毛病,簡直就是所有希望成為壞男孩的乖小孩無比向往的精神偶像嘛。年歲漸長,我也到了李尋歡輝煌登場的年齡,沒有愛情,也沒有飛刀,卻逐漸領悟到“尋歡”應該是這個時代最生動的精神符號。人生而尋歡,卻總是無可奈何地落入不堪,憂傷的欲望總是站在詩意的背面。
《折疊術》的創作,起源于一場小病。去年夏天,有一回參加一個比較嚴肅的活動,我站起來說話,突然感覺天旋地轉,有點站立不穩。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狀況,當時心很慌,但還是面帶微笑,強忍著堅持把話說完。幾分鐘之后暈眩停息下來,但腦袋里仿佛一個螺絲松動了,說不出的難受。活動結束,下了電梯到了酒店大堂,一個朋友看到我,在背后叫我,我轉身應答,但這一轉身不得了,天旋地轉,整個笑容都僵住了,扶著旁邊一個陌生人才站穩。朋友嚇壞了,趕忙過來扶住我,問我怎么了,要不要送醫院。我說有點暈,他們說可能太忙沒休息好。
想想,可能真的是沒休息好,那段時間太累了。太累那就多休息,于是接下來的整個周末我幾乎都在睡覺。但睡覺并不能解決問題,整個天地快要翻轉過來的感覺依然持續,特別是睡覺翻身的時候,更加離譜。躺下和起身也是,轉身彎腰也是,反正一動就暈。我內心充滿了絕望,幾乎崩潰。我不敢跟家里人說,怕嚇到他們。我打開微信想在醫院預約掛個號去看看,但發現連看哪一個科都不知道,我心想,我得先弄清楚我自己是怎么了,我要死了嗎?若真得了絕癥,剩下這么點時間我得另做安排。
反正暫時還不會死,我在網絡上瘋狂搜索,終于萬能的互聯網還是給了我一個答案:耳石癥。原來我們的耳朵里也有一塊瘋狂的石頭,它負責平衡,只要移位了,就意味著整個世界隨時翻轉。我苦笑了一下,繼續搜查解決辦法,網絡上有許多耳石癥的復位術,看起來就像一個體操。我幾乎看完所有的圖片和視頻,內心稍定,開始照著做。其實就是把我的身體折來折去,把那塊該死的石頭挪回原來的位置。我做了一遍,覺得不放心,又再做一遍,坐定,整個世界好像慢慢恢復了秩序。
做操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伊恩·麥克尤恩的《立體幾何》,他里面的幾何折疊能把人變沒了,多么神奇。于是有了這篇《折疊術》,嚴格上講,小說中并不存在什么神奇的法術。與我之前小說中分身術的設定不同,折疊術更多是一種生存感覺。或者說,分身是欲望膨脹的表征,而折疊則是欲望向內坍縮的結果。
耳石癥給了我一個啟發,我想換個角度,從故事的背面來寫故事。也就是說,《折疊術》中其實潛藏這一個故事,那里面打打殺殺刀光劍影,至少是兩起命案,但我都繞過去,我從另一個跟這個世界關系不大的人物寫起。我也不知道自己做到了沒有,但至少,我有意識在變換講述故事的角度,嘗試去寫一個意興闌珊的中年,一個人如何被激發,又如何被熄滅,最后撞向了一塊石頭。
這個集子里的故事都發生在虛構的碧河鎮,那里碧河流水,叮咚作響如小詩。這十二個故事,也是十二個平行的時空,十二種憂傷,十二支孤獨之歌。你若足夠細心,還可以發現它們之間居然也有一些關聯,彼此呼應,篇目之間都是好朋友。如果你讀過我的其他中短篇小說,大概也能看到有些人物會在這本書里面與他的命運繼續遭逢。
當然,把它們放在一起也會有問題,因為它們并非寫于同一個時間,創作的時間跨度甚至超過十年。這也意味著我必須花費更多時間來修改它們,使其有理由放在同一個集子里。
修改意味著重讀。重讀以前的小說,這種感覺像什么呢?就如我非常喜歡逛寺院,與大佛相比,我喜歡看十八羅漢,喜歡欣賞他們的神情和動作。在我看來,小說有長篇和短制,長篇應該是如來佛祖或者千手觀音,而短篇小說就應該是羅漢,像羅漢那樣精致、靈動、歡騰、安靜、務實、緊湊,總之豐富各異而又非常有表現力。優秀的短篇小說,應該是可以像羅漢一樣平等地擺放在一起,無論是掄著棒子還是手結定印,都能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
花費時間修改小說,看似比新寫一個小說不劃算,但其實也給了我返觀過往的機會。我慢慢意識到我精神地理的遷徙,開始從“半步村”到“碧河鎮”,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會走進“美人城”。這確實也符合我的成長軌跡,從農村到城市,或者說人在城市,卻也心心念念農村的種種物事。我的世界版圖在擴張,我的碧河在往前方延伸,我并不知道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在電影《2012》中有個場景:末日來臨,總統女兒和科學家討論文明的價值時提及一本賣不了五百本的書。黑人科學家說,這本書因為被他閱讀,所以也“已經成為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了”。我寫著,也和其他人一樣,常常懷疑寫作的意義,也懷疑究竟有沒有五百個讀者認真讀過我的小說。大概夜路總是要走的,秉燭總比摸黑好一些。就如一只鳥輕輕停落在枝頭,而它的爪子握住樹枝的一瞬,就注定終于還是必須飛走。
創作年表
短篇小說《我的恐懼是一只黑鳥》刊于《作品》2009年第二期。
中篇小說《半步村敘事》刊于《作品》2011年第一期。
中篇《黑鏡分身術》刊于《花城》2013年第三期。
短篇《結扎》刊于《中國作家》2013年第四期
短篇《玉蛇劫》刊于《人民文學》2014年第四期。
短篇《碧河往事》刊于《收獲》2015年第一期。
短篇小說《口罩》刊于《作家》2017年第九期。
短篇小說《虛度》刊于《江南》2018年第三期。
主要著作
2008年12月,小說集《宿命飄搖的裙擺》由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 。
2009年8月,詩集《只能如此》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
2010年7月,小說集《此外無他》由云南大學出版社出版。
2015年3月,中篇小說集《半步村敘事》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2015年8月,小說集《我的恐懼是一只黑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2016年3月,寫作入門書《正解:從寫作文到寫作》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
2017年7月,中篇小說集《黑鏡分身術》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18年7月,小說集《折疊術》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