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李德南:加前綴的現實主義
更新時間:2018-12-10 來源:長篇小說選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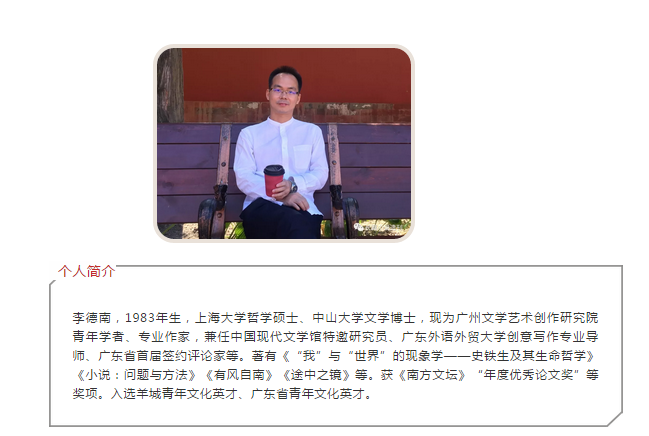
1854 年,法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大師福樓拜曾在一封書信中談到 :“我們這個時代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歷史感。這一歷史感強調歷史與眼前事實的聯系。所以我們在這一歷史感的影響下無不專注于事實層面的觀點、考察。”在福樓拜所生活的時代,對于“歷史”與具體的、可觀可感的“眼前事實”之聯系的強調,是現實主義認識論的中心特征。在那時候,現實的變化是慢的,允許人們徐徐感知,從容打量。未來的面影,總要經過挺長的一段時間才出現在人們眼前。人們甚至會經常覺得日光之下,并無新事。偏重“以史為鑒”來理解眼前的現實,是一種有效的方法。然而從 20 世紀以來,情形已大不相同。現實的種種構成因素,開始加速度地分化與重組、消亡與再生。要對現實進行判斷, 需要比以前更敏銳。歷史依然非常重要,但新現實的不斷涌現,導致了一種認識的斷裂。如今,要認識現實,在以史為鑒的同時專注于未來,變得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對未來有所認知的話,我們所試圖理解的現在會迅速地成為過去,甚至根本就把握不住現在。現實與未來之間的關聯,開始變得前所未有的緊密,似乎未來就是現在 ;對現實的洞察力和對未來的想象力,也早已變得不可分割。
現實在加速度地變化,時間在加速度地前進,風云變幻之快,似乎開始超出人們的預期和想象。文學也同樣如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 鄉土文學一直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潮。從中國當代文學以往的發展軌跡來看,在鄉土文學主潮之后,城市文學應該是順勢而生的文學主潮。可是城市文學這一后浪還沒來得及呈澎拜之勢,更新的科幻文學浪潮就出現了 :劉慈欣、郝景芳先后獲得了被譽為科幻界最高級別的獎項“雨果獎”。《花城》《上海文學》《作品》《青年文學》等刊物,先后推出了或計劃推出科幻小說的專輯或專號。不少之前主要被認為是屬于純文學領域的“傳統作家”,都開始著手寫科幻小說。科技的問題,還有科幻文學 , 也開始成為諸多文學活動、學術會議與學術刊物的重要議題。文學主潮的發生,并沒有按照鄉土文學、城市文學、科幻文學的順序來推進,并且城市文學很可能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已經無法形成主潮了。城市文學,也包括鄉土文學,很可能會被科幻文學所吸納,或是被科幻文學的浪頭所覆蓋,成為一種相對隱匿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股科幻文學寫作熱中,有一種可稱之為“未來現實主義”的寫作路徑。李宏偉的《國王與抒情詩》《現實顧問》, 王十月的《如果末日無期》,王威廉的《野未來》《地圖里的祖父》,郝景芳的《北京折疊》《長生塔》,都屬這一范疇。“未來現實主義”這個提法,我最早是在讀李宏偉等人的作品時想到的。后來我發現,王十月在《如果末日無期》中已經開始使用這個詞來命名他最近寫的科幻小說,不過他在小說里并沒有對何謂“未來現實主義”進行闡釋。這些作家的上述作品,通常以新的現實主義認識論作為根基。相比于以往現實主義者對“以史為鑒”的偏重,他們更重視的是“以未來為鑒”,是要以未來作為方法。這些作品的故事時間多是發生在不久的將來,有時候也直接寫到當下。這些作品中的將來,離我們著實不遠,甚至很近。故事中的一切,雖然并非都已發生,有的很可能不會發生,但是作者所設想的一切,都是有現實依據的或是有現實訴求的。他們都表現出一種意愿,希望看到未來的不同景象,從而更好地理解當前的現實 ;或者說,他們試圖勾勒或描繪形形色色的可能世界,繼而作出選擇,力求創造一個最合適的現實世界。
這樣一種寫作,可以說是當下非常有現實感的寫作。這些作家所注目的現實,不是陳舊的甚至是陳腐的現實,而是新涌現的現實:現代技術在加速度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甚至是改變著人類自身。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 使得人的主體性,以及相應的人文主義的種種知識和價值都受到巨大的挑戰,形成了存在論、知識論和價值論等層面的多重危機。
這種“未來現實主義”的寫作,和之前的現實主義寫作的不同之處還在于,傳統的現實主義非常強調細節描繪的細致和場景再現的逼真,而在當前的未來現實主義的寫作中,作家們不再致力于照相術式的逼真再現,而是吸納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學的表現方法,努力抓住基礎性的真實 :當今世界是一個高度技術化的世界,技術幾乎延伸到了一切跟人有關的領域。我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其實是跟技術的問題疊加在一起的。不管是討論肉身的還是精神的問題,是討論經濟的還是政治的問題,其實都需要以科技作為背景或視野—— 這可以說是當前時代的根本特點。
其實早在多年前,海德格爾就指出,西方歷史是由這樣三個連續的時段構成的:古代、中世紀、現代。古代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哲學,中世紀是宗教,現代則是科學;現代技術則是現代生活的“座架”,是現代世界最為強大的結構因素。最近幾年,人們著實體會到了現代技術的“決定性作用”,并因此產生了一種存在的興奮感或緊迫感。那些被認為是屬于純文學領域的“傳統作家”之所以關注科幻文學并寫作科幻文學,并不是因為以前主要是作為類型文學而存在的科幻文學有多么重要,而是今天的現實讓科幻文學這一文學樣式變得無比重要。與此相關,王威廉最近在一篇創作談中談到他有意嘗試一種可稱之為“科技現實主義”的寫作, 李宏偉則把自己視為一位“現實作家”,他們都把自己的寫作看作是現實主義的。
雖然當前的現實主義寫作有新的變化,但是現實主義的一些典律并未過時,比如從總體上認識人和社會的訴求。對社會的未來和人的未來的發展趨勢進行總體把握,仍舊是文學至關重要的任務。只是在今天,總體性或總體視野比之前要寬廣得多——不只是從社會歷史的世界視野來認識現實,更是要從宇宙的視野來認識現實。在這樣一個視野中,我們可能會發現,人類正處在經驗斷裂、知識失效、價值破碎的境況之中,我們得重新認識人類自身,得重新認識我者和他者的關系,得重新認識人和宇宙的關系。
除了未來現實主義和科技現實主義,早在多年前,就有學者提出“科幻現實主義”的概念,用以強調科技和現實、科幻文學與現實及現實主義的關聯。新一代的科幻作家陳楸帆亦認為,“科幻是最大的現實主義”。這種種有關科幻文學和現實主義的命名,其內里有相通之處,也各有側重 :未來現實主義側重的是從認識論、方法論的角度入手,強調要以未來作為方法。科技現實主義則從內容、主題的角度入手,側重強調技術已成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結構因素,強調當代世界的高度技術化這一根基性的現實。科幻現實主義,則側重強調科幻小說這一文學樣式對于探討現實問題的意義。
安敏成在梳理現實主義這個詞在西方的晚近歷史時曾這樣說道 :“對于西方批評家來說,它已成為那些令人尷尬、看來要求助于印刷手段以示區分的批評術語中的一個;在使用這個詞時,他們常常要加上引號,或以大寫、斜體等方式書寫, 以期使自己與它所假定的、現在已十分可疑的認識論拉開距離。當批評家可以輕松地談論古典主義、表現主義、甚至是浪漫主義而不必擔心自己會草率認可支撐它們的模式及理論前提的時候,最近有關‘現實主義’的討論卻無一例外地開始于對該詞的自衛性限定。以語言學為基礎的當代批評已卓有成效地顛覆了那種認為一個文學文本可以直接反映物質或社會世界的現實主義假象 :讀者被提醒,一部小說是一種語言建構,其符號學身份不能被忽略......西方當代的現代中國文學批評家們,敏感于文學模仿論之中的諸多哲學困境, 甚至已經厭倦談論現實主義。”安敏成指出了現實主義的理論困境,但他同時指出,西方人并未完全拋棄這個詞,“現實主義仍然強有力地規范著西方文學的想象”。而在中國,現實主義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當然,現實主義如此緊密地和科幻小說聯系在一起,還是有些讓人意想不到。
對于這種為現實主義一詞加上未來、科技、科幻等前綴的方式,我并不排斥。我認為這是一種調整方式且認為這些詞的內涵尚有待進一步深化,亦有待進一步接受檢驗。如果現實本身是變動不居的,那么也應該把現實主義視為可以不斷調整實際上也在不斷調整的概念和方法論,加前綴未嘗不是調整的一種方式。也只有在調整與更新當中,現實主義才能保持應有的活力和效力。這是真正的現實主義精神,也是現實主義的魅力所在。
【作者系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專業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