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楚些:王威廉散文——一種客觀詩人式的陳述
更新時間:2018-06-14 來源: 楚些 散文新觀察
主觀詩人與客觀詩人的提法為王國維先生所創,在《人間詞話》中他有過這樣的判斷:“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作為中西文論的匯通者,他所言的“詩”實指文學,“詩人”即白話文學語境中的“作家”。從觀念的嬗變來看,重主體表現還是重再現客體,兩種理論此消彼長,從古希臘一直糾纏到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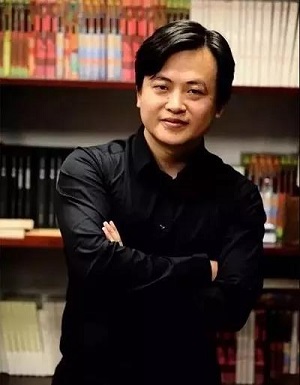
中國古典的文學體式以詩文為主,與之相關的則是詩學理論對主觀性的強調,諸如詩言志說,童心說,性靈說皆可作為注腳。近些年來,散文領域內抒情的因素雖然在弱化,然而情感投射不過是由外顯過渡到潛隱,經驗、自我、情思三個要素依然作為散文的核心要素而存在。從《城門開》《巨流河》到格致、塞壬、傅菲、李穎等人的作品,可做管窺。不過,變化總是有的,散文畢竟是個包容萬象的文體,反映在審美情態上自然體有萬殊,就拿80后散文陣容來說,趨于客觀性陳述的就有兩位,內蒙的安寧與廣東的王威廉。
安寧以寫鄉土見長,她筆下的鄉土風物如同風情畫一般撲面而來,閱讀之后,很容易代入,而少念及作者的性別、性格及情感狀態。安寧筆下的客觀性主要依靠以下三個因素加以完成:敘事的間離化,筆調的不疾不徐、不冷不熱,去情感化的寫作策略。王威廉擁有小說家的身份,令人意外的是他極少將小說寫作的技法與策略帶入到散文寫作中去,而是建基于人文主義的思維方式,以思辨的方法去端詳筆下諸事物,并努力使之實現現象學的還原。如此以來,一種客觀詩人式的格調在作品中被確立。
王威廉散文的取材,多選自日常的他者,其對微小之物似乎情有獨鐘,城市高樓間的樹木,玩游戲的孩子,街上的乞丐,服務人員等各種雜色人物,以及飯館、
草坪、燈光、貓咪等身邊之物。它們皆是陌生的他者或者經過重新打量后走向陌生的他者。比如《我見過一個人》這篇作品,由十個小段落組成,分別對應十個不同社會身份的人,他們皆曾與“我”有過短暫的交集,卻顯然又是典型的陌生的他者,如同我們每天與之擦肩而過的人們。

作者寫這十個人,并非是為了灌注或崇高或惻隱或敬重或鄙薄的情感,而是以此為基點,探討人對他者的認知,人與世界的關系,并以此為鏡像,確立自我思維、情感的存在尺度。比如作品中描述了兩個社會身份等同的乞丐,一位是體格健美手持黑色木笛的老者,神態蕭散而怡然,他專注于自我的世界中,一段笛聲或一縷清風即可成為遮蔽全世界的一場大雪。他的自在自為與遙遠的希臘化時期的第歐根尼形成了精神同構的關系,總之,他的存在暗示了這個世界風神瀟灑的一面;另一位則是佝僂的侏儒,蒼老的頭顱安插在變形的軀體之上,給與路過的行人以驚異,這種驚異之感過了頭,實則包含了恐懼和本能逃避的內容。她的存在,激發了人們身上潛在的集體無意識,即出于安全的需要對丑陋變形之物的恐懼和排斥,劉邦為何斬殺兩頭蛇,中世紀的教會為何將女巫妖魔化并送上斷頭臺,皆同此理。兩位乞丐歸置在一起,美與丑形成鮮明的對比,更重要的是,這美與丑與周圍世界所形成的關系層次,才是王威廉藝術處理的焦點所在。
或者可以這樣說,作者對羅丹《老妓》式的化丑為美并不感興趣,而是將重心放在逼近美與丑各自的生存真相上,指出存在的不同向度及世界自身的凸凹不平,這也許是殘酷的,但恰是真實之一種。薩特曾言人生是一種不能超越其不幸狀態的不幸意識,康德說任何一個個人從幾乎已經成為自己天性的那種不成熟狀態中奮斗出來,都是很艱難的。超越了,就是一種福音的存在,可以觀照出意義;不能超越,就是一種活著,可以審視其局限。除了身邊的微小之物以外,王威廉也寫了一些相對大一些的東西,但對這些對象皆未采取全景式俯瞰的角度,而是取一個原點,對這個原點加以思辨,加以生發。
在《藏地札記》中是信仰,在《德令哈隨筆》中是一座荒涼的邊城,在蝴蝶谷的行旅之途中是對其名號的辨析,在談荊軻的篇章中抽離出的是荊軻的符號性意義。就取材而言,面對自己最熟悉之處——自我經歷層面,王威廉少有言之。散文是一種對自我經驗高度依賴的文體,一般意義上,人最熟悉的疆域由自我為中心串起來的系列生活組成,再狹小點,就是一個人的愛情、親情、友情的經歷,大多數感人至深的篇章皆落定在這個狹小區域內。以上三種感情的綻開顯然不是王威廉的為文之道,某種意義上,他更像是位喃喃自語者。
那么,陌生到底意味著什么?王威廉筆下為何傾心于對陌生之物的考辯?文學是人學,人作為個體與外在的世界在關系層次上,陌生始終作為常態而存在,畢竟個體僅僅是“這一個”,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同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之中”!他的交往與感知與整個世界的寬闊相比,微不足道。由此可知,陌生之物填充了我們的人生過程,好奇心與求知欲不獨是科學的催化劑,也是文學的催化劑。
因為鐘情于陌生之物,感知的細密與感性的表達在王威廉散文中無疑遭受到了壓縮,一種不同于文史隨筆的思辨方式被確立起來。文史隨筆中的思辨主要借助歷史材料、時間空間的因果鏈得以完成理性的邏輯推理與歸納。而王威廉則主要借助類比,借助認知的積累完成對事物的勘察。這種思辨方法的后面矗立著人文主義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肇始于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他認為人文或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導致人們行動的內在意義,人們應該從日常的、平凡的事物出發,研究人類對社會現象做出的解釋以及賦予它們的意義,而不是簡單地還原于自然規律的水平。因為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而非“說明”。這就是說,社會學研究應該立足于微觀層面對社會現象進行分析,試圖站在對方的立場,來理解和解釋社會現象出現的原因。王威廉的寫作當然不是一種社會學研究的范式,他只是借鑒了這種思維方式,通過散文試圖拓展其對陌生世界的認知維度。如同荷爾德林宣揚的那樣:誰曾想到那最深刻的/誰便愛那最現實的。

作家王威廉
且以寫貓的《第一課》為例。東北作家沙爽今年新出的散文集《拈花》的前兩篇,所寫內容即為居家之貓,作者以準確而生動的文字再現了“塔塔”這只貓的成長、發情、社交的歷程,寫到了它的萌態和怯懦,寫到了貓的江湖里的交往法則,作為人間鏡像的投影,端立在視界之中。很顯然,從情感態度上,沙爽將這只貓視為家庭成員之一,在藝術處理上,她也將其人格化,而眾多寫動物牲畜的散文篇章中,人格化是一條普遍的路徑。而在《第一課》中,王威廉則去其熟悉,寫其陌生,努力讓貓媽媽與三只幼崽客觀化。其中,三只幼崽的關系,母貓癲癇病的發作,一只野貓的闖入,為陌生性的主體內容。對于“我”而言,只是一個發現者與思考者,對于眾貓而言,上述三個細節則是全新的內容。王威廉在這里采取了以物觀物的視角,盡量以貓的視角來思考貓與他者,貓與主人的關系層次。人格化之所以成為普遍法則,原因大概在于人常常扮演了低等級生命的上帝,自認為人是萬物之靈長的潛意識。而超越這種意識,當然需要自覺的思維訓練。
就散文的技術處理而言,思辨和哲思容易被混淆,兩者實則區別甚大。提煉哲思往往會采取兩種方式,其一為警句的直接宣示,紀伯倫《沙之沫》,泰戈爾《飛鳥集》《園丁集》,皆是這個路子;其二是通過故事加以間接地暗示,古老的寓言體,林清玄的散文,大體如此。而思辨的確立往往通過一個原點,借助理性力量和邏輯訓練,剝析掉泡沫和浮華的東西,進入思維的深處,得以還原事物的真實面目或者本質所在。毫無疑問,思辨性散文在情思的感染力上有所欠缺,但在識見能力上恰好應和了散文作為智慧文體的文體特性。新世紀以來,南帆、汪民安兩位學者的散文,堪稱思辨散文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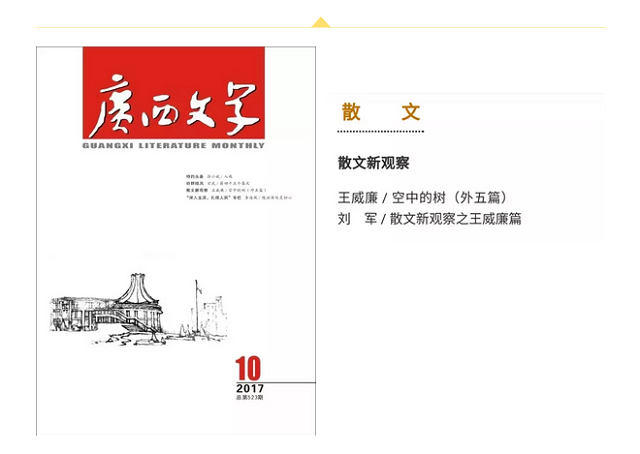
《廣西文學》2017年第十期推出了王威廉的散文《空中的樹》,由六個現實之思構成,分別對應了高樓間的樹木、個人身份證、眩暈感、孩童游戲、寫作的指向、個體的無力感,它們不是獨特的個人經驗組成,對于現代都市生活的人們來說,它們是一種普遍性的存在。在這里,作者借助短章向讀者呈現了其認知的成果。文學和哲學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較真”之道,盡管要遭受虛空的折磨,依然努力在“虛無”中開掘出意義、本質的命題。
迥異于他這的思維方式,思辨的深入,使得王威廉散文在風格情態上趨于理性,也推動其散文向著深度的開掘進發,但這些因素并不排斥表達上的豐潤以及感性細節的描摹。但這樣的寫作方式必然耗費大量的腦細胞,一旦出現應制之作或者急就章,一種明顯的扁平與虛弱就會彰顯出來,寫梅嶺古道的篇章,寫蝴蝶谷的作品,就是如此典型的案例。
楚些,本名劉軍,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散文批評家。曾任第一屆孫犁散文獎雙年獎評委,北大培文杯創意寫作大賽評委。現主持《廣西文學》《奔流》散文欄目。
王威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收獲》《十月》《作家》《花城》《讀書》等刊發表大量作品。獲首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文學獎、十月文學獎等。出版有長篇小說《獲救者》,小說集《內臉》《非法入住》《聽鹽生長的聲音》《北京一夜》(臺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