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虞宵 | 《越人城記》
更新時間:2017-08-17 來源:南方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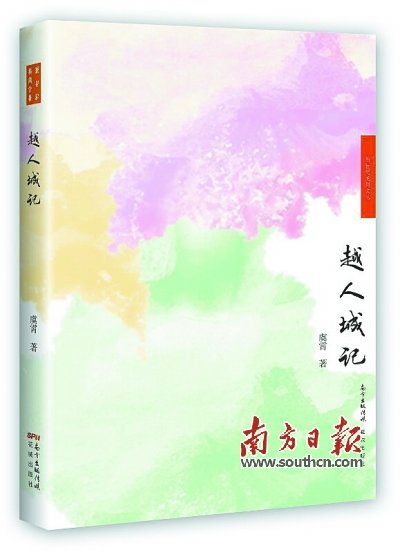
《越人城記》虞宵 著
花城出版社2017年5月
●周松芳
書評書話
美學上有距離產生美一說,亦即所謂的審美距離說。文化上也一樣。本地人說起本地的好來,往往像民科,雖大言炎炎,然每不能切中肯綮,為人所尊信,倒是外來者,久居斯地,由于存在一個原有的文化參照,對照比較之下,說起斯地文化,最易發現和發掘其相對優勢以及絕對美好的部分。今人如黃樹森先生,微名楚騷客,以志不忘為楚人,然畢生致力弘揚嶺南文化,雖年逾80,仍灼見逼人。近人汪兆銓,雖占籍番禺,亦不忘故鄉山陰(今紹興),特編《山陰汪氏譜表》,然更傾情傾力于表彰弘揚嶺南文化,編纂《番禺縣續志》,輯錄《廣州城殘磚錄》,撰述《廣州新出土隋碑三種考》等,尤其表彰粵人遺民精神,編纂《元廣東遺民錄》,開啟嶺南文化精神新篇章,并以身踐履,堅為遺民,最具風范。其師陳澧,最為一代巨儒,雖時署江寧郡望,亦最為表彰嶺南;其特著《廣州音說》 發凡粵調,稱“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即可見一斑。平生著述百余種,最足表征嶺南。凡此皆久居嶺南者,即如贛人湯顯祖,雖初履粵地,即縱情歌唱,所撰《廣城二首》:“臨江喧萬井,立地涌千艘。氣脈雄如此,由來是廣州。”一改以山水形勝言氣脈之慣例,而代之以喧騰之萬井與千帆并泊之珠江,最為灼見,堪稱歷史上詠廣州之最佳篇章。
有鑒于此,當我讀到虞宵的《越人城記》,不禁眼前一亮,心有戚戚焉。虞宵祖籍浙江,誠可稱為越人。入粵之祖,官至禮部侍郎,相當于今日文化部副部長,這一文化基因,更強化了其越人記憶,雖然后來占籍粵北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混入壯族血統。然而,嶺南與江南曾同為百越之地,史書上也屢有“粵越一也”的表述,虞宵也正以“百越”彌系其越地的精神追尋與粵地的現實感懷。因為有越人精神形成的相對距離感與觀照,虞宵的粵地城記便有一種在在的新奇感。
在《三城散記》中,她寫她讀大學和兄嫂母親生活的廣州,只是以十分質樸的散文的語言,卻最為傳神地寫出了廣州人的性格和生活特征,遠勝過那些長篇大論的論證。如說廣州的吃是:“滿街美食牽住人們的味蕾和胃,也是人們畢生最執著的追求。那些彌漫在街頭巷尾里隱藏的和味牛雜、手磨芝麻糊、雙皮奶姜撞奶、蓮子雪耳燉雪梨、竹升面蝦子餛飩,別有一番滋味,是這座城市最暖心暖胃的誘惑。”如寫廣州人的淡定是:“人們生于斯,更愛斯,不喜與人爭端,既來之則忍之,甚少惡語相向,怒目而視。實在話不投機,大不了閃開,躲到一邊,過自己的小日子去,井水不犯河水,各自精彩。”如寫廣州人的包容是:“這里自古就接納、收留來來往往的移民、流民。大官也好,貧民也好,來了就住下,要走也不強留,各安天命……碰到外鄉人有誤解、有疏離,他們一笑置之,當中,有妥協,也有堅守。”這是筆者從事嶺南文化研究十數年來所見的最精彩的文字之一。
她寫深圳這個移民城市,也正是著眼移民者“入鄉隨俗”而成的特有的性格與生活特質,在說完了幾個身份性格各異的女性移民的故事后揭示道:“她們性格各異,卻無一例外地熱愛生活,熱愛這座城市,以一名深圳人為榮。她們憑著潛力、勤勞、聰明、折騰,加上一點蠻、一點犟、一點橫、一點烈,再加上中國女人特有的溫良恭儉和男人般的埋頭苦干,讓這座城市閃爍著不一樣的光芒。”真是精彩而深刻。其長篇的《發廊簡史》,以及寫出租屋生活的《生死遺忘》和大排檔記憶的《大城小食》,角度之妙、體察之深,也是出類拔萃的。
寫罷后來長期居停的廣州、深圳,再回過頭寫少時的故鄉時,虞宵重頭的篇章竟是《頭牲簡史》——頭牲即牲畜;在鄉間是僅次于耕種的生活乃至生命的寄托,特別是在集體經濟年代,更是在不用心的耕種之外,農家最傾力傾情的對象。即便在小縣城之中,家家亦設法飼養各種禽畜乃至魚。同時,頭牲在山區小縣城里,也常常充作兒童的寵物和玩伴——這是多么別開生面的寫法呀!
由于身懷一種特有的他鄉關照與故鄉情懷,除了越地城記,筆觸及于外鄉外國,無不有一種親切的記敘。“扶桑之桑”,引發種種漢和的比類聯想;“大阪的城”與“東京的東”以及“京都的都”,即便從標題上你已經可以感覺到其妙趣所在了,其實在作者的筆下,仿如久遠的故鄉。回到國內,更是如此。如說:“江南水鄉與嶺南水鄉各自各精彩。只是江南的更顯文雅一些,嶺南的則多了一些潮熱生猛。”——“在西塘,配上昆曲,如在荔枝灣,配上粵劇。”
行文至此,甚覺虞宵之文有一種奇氣,而其人更有一種奇氣。比如說,她不僅喜歡喝酒,也還喜歡陪酒,而且從小就陪嗜酒如命的父親的酒——自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才是對酒最好的詮釋和尊重。多么雅的自我解釋呀!更顯奇氣的是,小時候天天纏著父母買沙袋練拳擊,買劍練技擊,不可得則自縫沙袋,削木為劍,同樣拳打腳踢,左劈右擊,儼然女俠。大約有此奇氣,始有后來的奇文,這正是優秀的散文難得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