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你站在這繁華的街上,感覺到從來沒有的慌張|廣東作家五人談
更新時間:2017-03-23 作者:曾楚橋、陳衛華等 來源:作品文學月刊

曾楚橋:寫作就是給自己找一個活著的理由
老實說,我很后悔選擇了寫作。這苦逼、無趣加無米的活計,我是怎么堅持到現在的呢?更奇怪的是,我為何至今還執迷不悟呢?文學真的能安妥我動蕩不止的靈魂嗎?我認真審視自己,難道我竟是傳說中的偏執狂?或者有純潔癖好的人?但我從來不曾以單純、善良自居,總覺得自己體內藏著不為人所知的黑,事實上,包括我自己,也不知道這黑會在什么時候突然蹦出來,我害怕它在我無法控制時傷害了別人。我貌似強大的只是軀殼,一個老丑的軀殼,實質內心是怯弱的,也是不可捉摸的。人性的復雜,我在不斷地自我審視時,一點一點地體會到了。
一個人如果在過了將近三十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仍然還能淡定地談理想,談風花雪月,談國家大事,薩得和愛國,那我可真的要封他一個圣人的稱號了。也許生活中還真的有這種令人景仰的圣人。顯然易見,我不是那種人。我做不到如此淡定。所以我只能一敗涂地的活著,在尊嚴掃地之后活著。然而,這世界的變化,我是看到了。那么我看到了什么?我能做些什么?我無力的筆能為弱者提供些什么?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一句話,我得給自己一點活著的理由。
是的,要找到活著的理由。所以我還在寫。僅僅是為自己找一個活著的理由。這話透著對世界的厭倦與極度不満。在過了憤青之年,再一次憤青起來,似乎不是好兆頭。于是便有了這篇《鯨落》。
在寫《鯨落》前半年時間,我一個字沒寫。期間,好友閆永群因病離世。他在重病中修改他的小說《一個平民的新聞發布會》時,曾和我說過,我們這一代打工人,馬上就要被歷史遺忘了。那些曾經受過的侮辱也將被歷史遮蔽。我即便死了,也不瞑目。
我是在他逝世后,才慢慢體會到他當時的心境。是的,死不瞑目,可能是他對世界最后的看法了。我內心的嘈雜,可想而知。多年來,那些自以為是的文字,突然變得如此不堪一擊。《鯨落》中的羅大春就是好友閆永群,我在文后也題上了獻給他。事實上,羅大春也是我自己。在完成初稿時,我沒頭沒腦地大哭了一場。很多年來,我寫的東西從來沒有感動過自己。這一次,算是有點例外了。其實也說不上是感動。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在哭什么。還是那句,我哭的是我自己。在自傷自憐之后,擦干臉上的眼淚,于是就慶幸自己還活在這個一團糟糕的塵世。
活著就意味著一切。不管你千億身家,還是貧困拾狗屎,都是兩手空空的來,最后還是兩手空空的走。金銀珠寶帶不走,狗屎也帶不走。當所有的一切指向虛無時,我得為活著找到一個可疑而且虛妄的理由,聊以度日。僅此而已。
曾楚橋,男。廣東化州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第六屆網絡作家班學員、廣東省文學院第三屆簽約作家。作品刊于《作品》 《收獲》 《中國作家》等,部分小說被翻譯成英文。出版有短篇小說集《觀生》和《幸福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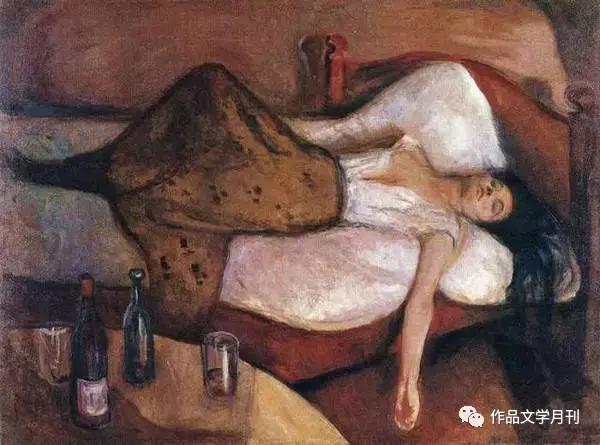
陳衛華:落魄,是生活的真實
小說寫完最后一個字,我吁出一口氣,然后加上一行,“2015年5月于無比落魄中”。
當時我有多落魄呢?公司瀕臨倒閉,身體多種疾病同時在吃四種藥,兒子中考因資料不符無法上公立高中,老婆因病住院。壞消息還在來,專賣店也開始虧了,公司年檢無法通過,連好好的打印機也說壞就壞了。還有一個建立在我痛苦之上的好消息是,前兩年為解決公司資金不足賣掉的一套房兩年漲了四百多萬。
巨大的身心壓力,讓我經常半夜失眠,感慨人生。有一天突然就有種強烈的沖動,我要寫點東西,是該寫點東西了,停筆二十年了。
我用二十天寫完小說初稿,晚上有時寫到凌晨。盡管累,但總比失眠強。況且時間也不等我了,老婆雖然出院,但不能出門,我要去居委會核對資料,去街道打證明,甚至準備不行就干脆回老家一趟作揖下跪都成,為兒子能讀上公立高中做最后努力。公司年檢也要重新去工商局、國稅查詢問題所在,一步一步解決積壓問題。畢竟,這比寫小說事大多了。
就這樣拖著落魄的身軀,又上路了。
有文友說小說中夏風很落魄,灰色了點。其實夏風算好的了,現實中比他更困窘的人比比皆是。在深圳打拼過的人都知道,無論打工還是做老板,這座城市給人的壓力都非常大,每天有人負債絕望,每天有人卷鋪蓋折戟北上,尤其這幾年實體經濟萎靡和高房價,更破滅了無數人的深圳夢。現實生活本來如此,所以才會有文中真實的夏風。之所以說夏風還算好的,是小說畢竟要給人一點前行的溫暖,所以夏風后來遇上了一位好老板薛素萍,讓他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而現實中多少人還在風雨中吶喊,在淚光中迷茫,不一樣要懷揣勇氣生活下去嗎?
前幾月,在粵老鄉年會,好幾位老鄉喝得酩酊大醉,有哭的有流淚的,丑態畢現。這事其實年年都有。有一位老鄉五年沒回家了,他說來深圳十七年了,現在仍無房無錢無老婆,典型“三無”,內地教書的工作也辭了,還怎么回?一位說,七十萬的時候我沒買,一百五十萬的時候我沒買,四百萬的時候我拿什么買?大家都知道他說什么,但沒一個人說“房”字。有人說,讓他們醉吧,總不能壓在心里不讓他們發泄一回。老鄉年會,終成了落魄人不用偽裝的臨時皈依地。
小說可以給人前行的溫暖,但擺脫不了生活的真實,過多的心靈雞湯無助于人成長,只增加肥胖。
陳衛華,1967年生,江西鉛山縣人。1991年開始在江西日報、中國商報、星火等刊發表小說散文。1993年辭職來深圳打工,從事過行政經理、業務員、業務經理、廣告策劃、副總等多種工作。1997年創辦公司,幾度沉浮。1998年獲深圳華僑城保齡球館廣告語征集一等獎。2015年重新開始小說創作,有發表及獲獎。現居深圳福田。

阿微木依蘿:復活那條魚
我想在屋里刨一個大坑,從地下五十米的地方取水,讓坑道逐漸長出青苔,看上去差不多像一口老井。得瞞住所有人。可是這兒晝夜都有人通行,我的門對著巷子口。
這是無意義的事。
我想在對門栽一棵黃桷樹。是我家鄉那所縣城的黃桷樹的樣子。可這里堵滿了新的舊的房屋。我不是房子的主人。我僅僅獲得一小塊短暫的立錐之地,需要每月繳付租金來保障我可以繼續當一名合格的旅客。
這是無意義的事。
我的樓上夜間有人偷偷丟垃圾。我住在底樓。沉重的響聲砸在窗口外,有時也從窗口上方的頂棚落下來。于是,我準備開窗偷看具體是誰干了這么不要臉的事——如果幸運地捉住了,就要告訴他,我們這個片區的人的整體素質全都被他拉低了,他是罪魁禍首,如果他愿意悔改的話我可以原諒;如果不愿意,或者更加不幸,他會沖下來打我一頓。可是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我沒有開窗……不,也許開了,或者不是我而是別的什么人。反正等我睡醒一覺,月光就像刀片一樣割住我的半扇窗門。他們將我的平板電腦偷走了。
不值一提,這也是無意義的事。
我依然堅持說愛世上的一切要從愛一條陋巷開始。愛這兒的每一個人。包括偷走我東西的人也愛。他們白天從我門口的巷子里出去,在馬路邊擺上破三輪,上面掛一塊牌子:收舊家具。收舊衣服。搬家。拉貨。修家電。疏通管道。他們仿佛會干世上所有的活。臟活、累活、大活小活。也說笑話。也抽煙喝酒熬夜。
可這些也是無意義的事。現在我緊迫地需要做點有意義的事情。然而時間過了很久。我在這片地方快要耗光了青春。
如果我要去摘一個眾人僅有的月亮會成為公敵。可是我必須這么干。這樣才能把我和他們區分出來。
我便默默地在這個既不是故鄉也不是長久居住地開始了一系列的謀劃。然而,我的野心有多大失敗就有多大。我早就預知了。很多人也這樣過完了他們的一生。可我不在乎。如果我一直保持著獨自享有一輪月亮的理想,我就會一直不在乎。但我長期做夢,有時夢見自己發了大財醒來卻還是窮光蛋。就算這種心境根本不能做成什么,我也要堅持。很多事情在我腦海里飛。我必須記下來。我要告訴他們某種力量的存在。這樣才能把我和他們區分出來。
我不想躲在房間里寫東西了,而是想跑出去,到哪兒隨便畫點東西,比如畫一條岸上的魚——對,是岸上不是水里,一目了然,人們看了不需要思考就知道它活著但其實已經死了很長時間。這時候,我就要證明自己留住了什么,比如光陰,或者干脆復活那條魚。我會試著在眾人面前給這條魚一個完整的太陽和月亮,還有一大片海水——創建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對,不是那條陋巷的常態,是陋巷的反面。我要證明某種力量的存在。這樣才能把我和他們區分出來。
可是毫無意義。我什么也干不了。野心有多大失敗就有多大。我已經預知。很多人也清楚。
事情并沒有結束。我感到有了很多同伴,螞蟻般的舉著一束光。這算是一個好消息吧。他們起初也只想挖一口古井,在對門栽一棵樹,愛陋巷中的每一個人。但最后他們全都入魔般的只干一件事:走出門,到陋巷之外,復活那條魚。
這是無意義的事。螞蟻般舉起的那一束光,不太像一輪月亮。但誰知道呢。
阿微木依蘿,彝族,1982年生。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人。初中肄業。自由撰稿。現居東莞市。曾就讀于魯迅文學院。2011年6月開始文學創作。2012年發表作品。寫小說和散文。發表作品多篇。出版中短篇小說集一部。獲第五屆在場主義散文新銳獎。第五屆東莞荷花文學散文獎。第三屆廣東省“九江龍”散文優秀獎。第二屆廣東省有為文學獎——“大瀝杯”小說獎。

吳向東:用歷史的目光凝望歷史
小說《最后一道光亮》,雖說寫得是兩個老工人的故事,但我更希望它的讀者是中青年人。因為故事的主人公很可能就是他們的祖輩父輩,或者是他們在公交或地鐵上遇到的某個顫顫巍巍的老人。
我出生在武漢一個工業重鎮。那里原本是蒿草叢生的荒蕪丘陵。五十年代,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工人和學生匯聚于此。他們衣衫襤褸,忍饑挨餓,腳丫靠腳丫地睡在竹篷里,硬是在這片荒蕪的丘陵上,煉出了新中國的第一爐鋼,制造出新中國海軍的魚雷發射管。
在我少年的印象中,我家的房子,是由紅磚砌成的平房,那里一直是父親班組兄弟聚集的場所。大家抽著劣質的香煙,喝著幾分錢一勺的白酒,罵美帝,咒蘇修,研究技術革新方案,當然有時也會聊女人。
可不知什么時候起,他們忽地相互之間成了仇人,分成了兩個陣營,佩戴著各自組織的標志。他們頭戴柳條安全帽,拿著長矛上街。那長矛是用他們共同煉出的鋼鐵打造。
他們曾是能過命的階級兄弟,當他們拿起手中的矛刺向對方時,依然擁有共同的理想。可這理想沒能阻止他們成為仇人,卻讓他們的矛尖放著更鋒利的寒光。我想歷史并不是第一次演繹這樣的悲劇,不幸的是我成為了這場悲劇的旁觀者和見證人。
我一直想寫他們的故事。不僅是為那場血色黃昏后的搏殺,更為他們今天坎坷的命運。那場歷史大劇早已謝幕,歷史賦予他們角色也悄然褪去。而當新的歷史帷幕拉開時,他們中的大多數,必然淪為配角,被忘卻甚至被唾罵。可我們不要忘了,他們是共和國的長子。他們也曾創造出和他們兒孫們一樣的輝煌。
寫這篇小說時,我想起了大興安嶺的林場工人。他們激情勃發的青春,正被他們用汗水養育的后人,放在鍵盤上肆意地拷問。他們過去以伐木工人的身份為驕,以為祖國提供棟梁之材為傲。可如今有人卻說,那些在鏗鏘的號子中倒下的原始林木是他們的原罪。就如同那一排排我們曾經無限贊美過的,冒著滾滾濃煙的煉鋼爐的煙囪。
如今,風燭殘年的他們大多又走到一起。勝利者沒有勝利者的喜悅;失敗者也消隱了失敗后的落寞。他們依稀尚存的理想,讓他們面對當今變幻莫測的世界有了共同的困惑,也有了更多相同的情感。工業重鎮里年輕人越來越少,而留下的卻是他們耳鬢廝磨之間的懊悔和對往日激情的回憶。望著他們漸漸衰老的容顏,我時常會對自己發問:一群有著共同理想和目標的兄弟如何后來會盾矛相抵。
我相信:歷史只能用凝望而切忌不可輕佻的回眸。
吳向東,湖北大學物理系畢業。曾獲全國孫犁散文一等獎;廣東省大瀝杯有為小說獎;有中短篇小說及散文發表于《十月》《花城》 《小說月報》 (原創版) 《清明》 《芙蓉》等中文核心期刊物。

段作文:那些被歷史巨輪碾壓的生靈
面對這個時代,你可能覺得很好,也可能覺得不那么好,就看你處于何種角度站怎么去看去想去感受。
這些年,我所遭遇的人事,大都是來自底層的呻吟與妥協,偶有抗爭,也多以失敗收場。這些時代的棄兒,包括我自己,既有客觀因素,也有自身因素。這個小說就寫了這么一群人,他們的悲喜,看似可期的結局,說不定在哪兒就小說的原標題叫《挖砂》,寫到一萬字左右時,看起來像個不錯的短篇了。同事兼室友楚橋兄看過之后,覺得輕了點,不夠透徹,建議弄成中篇。
從短篇到中篇,無論語言、布局、故事還是格調,都得打亂,從頭來過。那是一個極其痛苦的過程,卻也有種莫名的快感。
初稿三萬五千字,一氣呵成之后,恰好在一次文學活動上幸遇走走老師,我非常誠懇地向她請教。看完稿子,她現場給了一些專業方面的建議,為后來的修改提供了一定幫助。
小說改了三遍,邊改邊跟楚橋兄就一些細節的真實性進行討論。待成稿時,它已被砍至兩萬七千多字。從構思到投稿,歷經三個月,那些日子幾乎天天都在捉摸這個小說。在決定寄出去時,我又把打印稿給其他同事看,想聽聽普通讀者的意見。這幾位同事有一個喜歡看網絡小說,他說能一口氣看完,我就高興了,說明還是有相當可讀性的。另兩位同事是深圳本地人,他們用家鄉話反復說著“挖”“砂”,讓我對老人家的言行有了更直觀的感受。
小說究竟說了什么,想說什么,這是作者的事。能讀到什么,感知到什么,想到什么,那是讀者的事,在這里我就不多說了。等它刊登出來,面對白紙黑字,認認真真讀一遍,再讀一遍,你就明白這《臺風吹過砂瀝街》究竟是啥味道了。那臺風究竟有多猛,砂瀝街究竟是條什么街,街上有什么不一樣的風景,大家就好好去品《作品》里的作品吧。
我在廣東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這是第一次在《作品》亮相,一發就是個中篇,還剛好碰到千字500元的稿費,確實令人驚喜。寫了這么多年,我是一個發表量相對較少的作者,每一次發表都令人興奮,大刊物高稿酬興奮就多一點,所謂的小刊物低稿酬興奮可能相對小一點。但無論怎么講,一個稿子能發出來,能有些收入,都是好事,都是肯定,終歸是值得高興的事情。在這個物質與精神倒置的社會,寫作作為一種愛好、心性或者樂趣,我覺得已經非常不容易了。在歷史巨輪的碾壓下,為那些弱小的生靈,為自己,寫出痛感,寫出性情,寫出真誠,我想,才是我們真正想做的,值得去做的。
記憶中這是第二次寫創作談。作品寫成后,人物、故事、命運就已經屬于作品了,在此,應刊物要求,我簡單說說寫作過程和感受。我會按自己的路子寫下去的,堅持一些,放棄一些,然后進步一點點。
段作文 ,四川廣安人,有中短篇小說發表于《長江文藝》《四川文學》 《特區文學》等。曾獲首屆“全國青年產業工人文學獎”、第五屆“深圳原創網絡文學拉力賽佳作獎”、第三屆深圳 “睦鄰文學”年度大獎、第二屆“兩岸三地短小說大賽”提名獎等,廣東省作協會員,現供職于深圳沙井街道文體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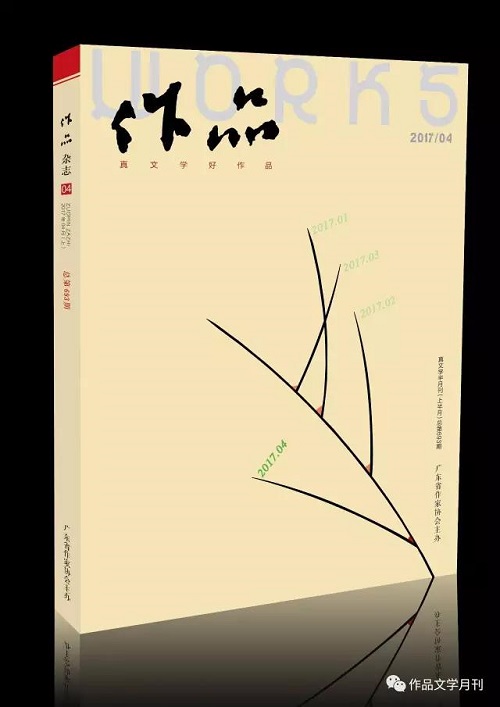
《作品》2017年第4期主要目錄
視 點
廣東文學的一手好牌
記 ? ? 錄 時代鏡像
小世界/海男
虛 ? ? 構 ? ? 敘事中國 ??
鯨落/曾楚橋
回家/陳衛華
魚在岸/阿微木依蘿
最后一道光/吳向東
臺風吹過砂瀝街/段作文
發 現 洞幽燭遠
刺客尼古拉耶夫身上的四張牌/王族
推 手 90后推90后(本欄目與《文藝報》聯辦)
最后一夜/丁顏(女)
囚徒困境/丁奇高(男)
手 稿
我們曾經小說過(外一篇)/汪政
漢 詩
長詩
長沙/雷武鈴
短制
草原歌者/鄭靖山
女人和她的馬(組詩)/遠心 ? ? ?評/樵夫
民間詩刊檔案(與《嶺南師范學院學報》聯辦)
《趕路詩刊》/任意好 ?張建新 ?等
“典型”立場論——趕路精神與當前漢語詩歌
尊嚴之我見/任意好
品 讀
封二/黃燈 吳佳駿 封三 /李銜夏 陳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