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張黎明 | 《她的老街:1979-1983》
更新時間:2017-03-08 作者:張黎明來源: 共同體Commu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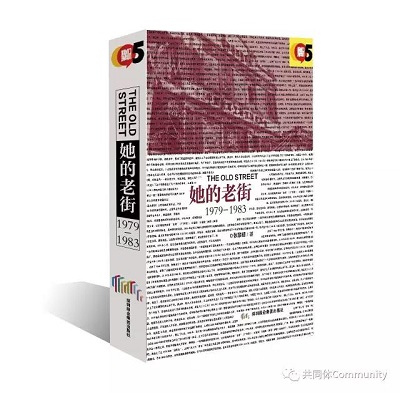
《她的老街:1979-1983》
張黎明 著
深圳墟
1979年那陣兒,深圳市人少,只有墟日是當時最聚人氣的時候。
深圳墟和墟日是兩碼事情。先說墟,佛山普君墟,升平墟面積大,有今天常見菜市場的好幾倍。1979年的深圳墟是市中心唯一的墟,比佛山墟小多了,是袖珍版,可趕墟的洶涌勁頭不比佛山遜色。深圳墟市濃縮在十字街人民路南段20米左右的盲腸地段,也就是2016年太陽百貨廣場東門口的那一小片。如今的地面還打了個銅標志,上面是一桿秤。
深圳墟北端緊靠解放路,南端聯通了七拐八拐的小街小巷。
深圳像佛山一樣也有常設的墟日。墟日,也就是趕墟的日子。
深圳墟墟日農歷二、五、八,還有特別的節日都是墟日。

熱鬧的墟市 ?(羅恩·策史葛 攝)
趕墟,她也有種說不出為什么的喜歡。她不明白這些奇異的鬧哄哄的趕墟,竟把一切吸引其中,包括她自己,那是不可拒絕的絕對魔力。
想想,或許這些從土地生長出來的味道就是現在所說的地氣。
日頭沒出,她躺在床上還沒有醒,就聽到了地表的聲音。四面八方的農家從朦朦朧朧的暗處涌出,有聲有色地,并非潤物細無聲那種細膩纏綿,而是穿過小巷踏踏踏地洶涌而過,三個五個成群結隊,浪潮一般急迫迫真切切地趕去了。
小巷也開始動了,嘩啦啦地開門,還敲打別家的窗戶,鄰居婆娘們的大呼小叫,還能不夢醒嗎?
她突然想起這是星期天,得補充點營養什么的,于是一跳而起。
墟里很鬧,許許多多戴涼帽的大腳客家婆娘和許許多多講圍仔話的本地佬,互相穿插混合在墟市里。買還是不買,賣還是不賣,這是唯一的問題,各自嚷著不同的方言卻互相明白透里,聲量分貝極高,看似吵鬧,實為毫無殺傷力的斗嘴……

1980年的鹽田墟海鮮市場如深圳墟一樣熱鬧。澳大利亞采石專家策史葛很納悶,為什么堆滿了一籮筐一籮筐的鮮魚?找不到答案只有“咔嚓”下來了 (羅恩·策史葛 攝)
一眼看去這些搖搖晃晃的扁擔都壓得彎彎的,吱吱呀呀的聲響不算啥,那籠子里的雞鴨鵝比扁擔的聲音高出數倍地大叫。雞、鴨、鵝這類小家禽,尤其是個頭極偉岸的獅頭鵝,真叫得人心頭發顫。
紅撲撲臉龐的客家婆,汗濕的衣裳貼緊脊背,黑色的大襟衫裹出結實豐盈的身段,可比跳龍門的鯉魚那樣有勁,坐或蹲,一雙大赤腳肆無忌憚或交叉或分叉擱在那些家禽的籠子邊上。遇到連老嫩母雞都分不清的她,人家一手抓了雞腳一手輕輕掰開雞屁股,一嘟嘴吹開細毛:雞項仔(小母雞)。
她根本就看不明白,也笑著點頭。
單車后架背著豬的赤膊佬,看起來瘦得一肋一肋排骨,不怎么有力,眉頭鎖得很死。背架上一左一右兩頭豬,少說也三四百斤,車胎也扁扁的,也不知道養了多少張吃飯的口,為生活,沒有法子。

策史葛跟著抬筐的漁農終于找到了答案,一望無際的海邊晾曬著魚。咸咸的風咸咸的味道,眼前是晾曬中的腌制咸魚!中國人最古老的保鮮方法 (羅恩·策史葛 攝)
最有趣的是賣蠔的女人,默默蹲在一角,不叫不喊。腳邊有一個小木桶,里頭有白白滑滑水淋淋的鮮蠔,賣蠔賣魚或賣蝦的都喜歡蹲在一起。她的臉黑紅透亮,皺紋不多,但每一道都如刀刻的深。這蠔取得不容易,一只只都是從那石頭縫里長出的,潮退的時候砸下來,再一個個撬出蠔肉,這等鮮美的東西,尋它的人多。皇帝女兒不愁嫁,賣蠔女子從來不吆喝。
大弟弟曾經提了小半桶這樣新鮮的蠔回家,說帶旅行團去蛇口,在蛇口買的。怎么做?用慢火煎干,煎得很軟很香,兩邊有一點兒金黃就行了。真的,吃過那樣的蠔后,想起也會不停地咽唾沫“返尋味”。墟市里的賣蠔人,不知道那蠔是否來自蛇口。
墟市里的人擠擠碰碰,她也擠進去這里看看,那里蹲蹲,聰明的人看上了自己中意的就掏錢。沒有討價還價,那時節人們還沒學會這一招,心里都清楚值多少,出天價或大砍特砍的事情絕對沒有,精巧聰明的潮州人還沒有大舉進軍深圳。
她笨,反應慢,不知道這洶涌的墟也像1979年的建材局那樣供不應求。出門趕墟這兒看那兒看,一輪慢動作過后,最后發現想買的都沒有了,不想買的也沒有了,很慚愧地趕了一個兩手空空,不知道她趕墟還是墟趕她……
散墟了。
日頭從東到西慢慢地走,人們也慢慢地從墟市往街心移動,漸漸像一條湍急的小河,不時涌入十字街,主要是解放路比較大的百貨店、新華書店等等,其次就是人民路的小店鋪。
趕完墟的大嬸和姑娘在布店里嘰嘰喳喳,售貨員噼噼啪啪地扯動布匹,剪刀一斜,藍斜紋花布就各有各的主了;靠腳營生的鄉民或是單車佬也不忘小城的理發店,經常把空的挑擔或運貨單車靠在門邊,人閉了眼靠在大躺椅里,也許心中盤算著這一趟凈賺了多少,該買點什么。打了個盹,發也理好了,摸出些零子,一角五分理一個發;也有的人懷里藏著錢,手里拿著空扁擔,一間間店鋪轉,這也好那也好,摸過了卻舍不得掏錢,這是留給阿妹上學的,皇帝老爺也動不得。
最熱火的是街邊小吃,“蘿卜粄”“糍粑”“炸蝦角”都發出誘人的香。掏出腰包,花一角幾分吃出一嘴油。要不,坐在小吃店來兩碗云吞面,高級點的就去新安酒家來一碟頭飯快餐、梅菜豬肉或者蘿卜牛腩。
深圳十字街1996年重建的時候,她特別留戀墟日,更想弄明白這深圳墟的歷史。它不是1979年墟日的那點范圍, 它的久遠要翻《新安縣志》,到底有多久遠?1909年廣九鐵路修成之前有它,割讓港島前有它。墟立何時?深圳博物館考證為明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距今六百多年。坊間有說清康熙二十七年《新安縣志》墟市條目中載有“深圳墟”,故得出深圳墟距今有三百多年歷史的結論。
這是記載日還是立墟日?她一腔疑惑去翻查史料,從隋唐至明清(公元581年至公元1839年),靠山面海溫暖濕潤的新安地域,盛產珠、蠔、鹽、漁、香,更有稻谷菜果,自然就有貿易集市。南頭、王母起始享有大墟之名時,琢磨那深圳墟絕對還是三個自然村之間很小的買賣場,此時是否更早于明永樂八年?這葉屋村、南塘村和油榨頭村,幾村之間的小墟集,如何年復一年越來越大?賣豬的漸漸多了,于是有了豬仔街;賣魚的也不甘落后,聚在一起自然成了魚街;酒米店和餅店以及布店、茶樓也自然而然地趕來了。
它如何靜悄悄地超越了不遠的湖貝,又如何與南頭遙相呼應?直到今天,深圳墟沒了,“深圳”成了這片地域的符號,深圳墟立何日終歸成了奧秘,這替換之中的偶然和必然,留給后人去猜想了……
而《深圳近代史》記載,康熙八年(1669年)復界,恢復新安縣,鼓勵原籍居民返鄉耕種,實行招墾提供種子耕牛以及免一定年限賦稅的優惠政策,東江流域、嘉、潮及閩贛兩省大批客籍農民遷入,漸漸恢復各種生產,繼而商業貿易空前活躍。
清朝嘉慶道光時期,新安縣的縣城南頭和縣丞署大鵬城和縣內其他人口集中之地共建有36個墟市,其中就有深圳墟。
這些墟市“有專門的商號,店鋪,如當鋪、布匹店、日用百貨店、咸雜店、鐵器鋪及其他農具等。農副產品成行成市,有豬行、牛行、雞鴨行、米谷行,荔枝成熟時節有專門的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