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南方日報》專版推介廣東作家實力新生代
更新時間:2016-10-21 來源:南方日報
實力新生代:廣東80-90后作家群像(上)
編者按
在剛剛評出的廣東有為文學獎中,80、90后青年作家占據大部分席位,可以說這些青年作家已經成為廣東文壇的中場發動機。廣東青年作家群的影響實際上已經越出本省范圍,跨過長江、黃河,走向全國。他們在《收獲》《十月》《人民文學》《花城》等大刊頻頻發表作品,并獲得了不少全國性文學大獎。他們不但人數眾多,而且知識背景完善、人生經歷豐富。大部分青年作家擁有本科學歷,王威廉、皮佳佳、林培源三人更是中山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博士生。在許多文學大省后繼乏人的情況下,廣東文學卻逆流而上,在南方乃至全國一枝獨秀,盛開繁華,使得廣東文學的“粵軍”呈現出良好的梯隊排列,后勁無限。南方日報文藝評論專欄將分兩期推出部分重點作家的評論,請讀者垂注。

荒誕、歷史和靈魂——王威廉的三副敘事面孔
王威廉
1982年生,先后就讀于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收獲》《十月》《作家》《花城》《讀書》等刊發表大量作品,并入選多種選刊、選本。獲首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文學獎、十月文學獎、首屆《文學港》“儲吉旺文學大獎”、廣東省散文獎、廣東省中篇小說獎、《廣州文藝》都市小說雙年獎等,入選廣東省青年文化英才。出版有長篇小說《獲救者》,小說集《內臉》《非法入住》《聽鹽生長的聲音》《北京一夜》(臺灣)等。現任職于廣東省作家協會,兼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創意寫作專業導師。
2007年,大學畢業不久的王威廉憑借著在《大家》上發表的《非法入住》初登文壇就引起關注。這篇作品很快入選《2007中國小說北大選本》并得到評論家肯定。王威廉是浸淫現代主義頗深的寫作者。九年過去,他已經出版了小說集《內臉》《非法入住》《聽鹽生長的聲音》《北京一夜》(臺灣版)、長篇小說《獲救者》,獲得過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文學獎、《十月》文學獎、《文學港》·儲吉旺文學大獎等許多獎項,部分作品被譯介到國外,被視為中國“80后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綜合看,荒誕敘事、歷史敘事和靈魂敘事成為他寫作的三張鮮明的現代主義臉孔。
《非法入住》是王威廉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描述的是極具當代中國特色的蝸居生活,王威廉將九平米的出租屋作為小說人物活動的全部空間,匪夷所思又絲絲入扣地演繹出荒誕敘事。“你”租住的九平米空間本已夠逼仄,可是鄰居的“鵝男人”一家居然三代六人擠在相等的空間中。有一天,“鵝兒子”、“鵝父母”、“鵝妻子”相繼要求住到“你”屋里去。由此,“非法入住”便次第拉開……
必須指出,小說情節不斷走向荒誕卻又始終堅守著牢固的現實情理邏輯。小說的看點在于王威廉如何將一個理念性如此強、如此不合情理的故事在現實經驗的底座上演繹得令人信服。小說由是也兼具堅實的現實性和深刻的寓言性。由《非法入住》始,荒誕成了王威廉最經常采用的文學表達式,他書寫荒誕,又始終沒有脫離當代中國的生活實感。王威廉小說跟底層文學分享著相同的時代經驗:《非法入住》與蟻族蝸居,《父親的報復》中的拆遷,《魂器》中研究者他的青年學者的學術工蜂生活,《當我看不見你目光的時候》中的視頻監控,《老虎!老虎!》中的“自殺”,《內臉》中的網絡交際,《秀琴》中的農民工傷殘,《沒有指紋的人》中的稀奇古怪的網購……所有這些都是鮮活生動、慘痛心酸的中國當代經驗。只是他的寫作由經驗出發而重構了經驗的深度,他的現代性透視能力使他在所有這些經驗中提煉出的“荒誕”并非僅是一種形式沖動。這約略可以解釋王威廉作為精神現代派跟先鋒小說作為敘事現代派的差異。
作為一貫被視為缺乏歷史感的80后作家,王威廉并未與歷史題材、歷史事件短兵相接,然而他荒誕的敘述卻常常顯露出直面歷史時沉重的嘆息,并發展起有趣的歷史敘事。在《水女人》這篇作品中,王威廉試圖觸及某種“歷史記憶”的建構和坍塌,因此跟中國現實有著更加密切的聯系。小說一開始,女主角麗麗在一次家中淋浴后失憶了,她艱難地面對這個對她而言突然完全陌生的世界。王威廉通過“失憶”將人物從慣常的世界中重新取出來,迫使他/她嚴肅面對生命的“被拋”狀態,并直面生命的破碎和重建。
《水女人》的“歷史記憶”話題必須跟王威廉的另一個小說《絆腳石》對讀。在一列廣州至深圳的高鐵上,圖書編輯黎曉寬與一個滿頭銀發氣質非凡的退休女教授蘇蘿珊邂逅。旅途的乏味使他們互相對彼此講述了各自的家史。作者特意將蘇蘿珊和黎曉寬的邂逅安排在這個時代的“高鐵”上,意在以不斷提速的當代生活為背景,提醒某種面對歷史適當“停頓”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蘇蘿珊還是黎曉寬,他們講述的都是上輩的家族故事。換言之,小說是通過“血緣”這層關系來呈現歷史記憶的。如果說歷史記憶可能被各種方式建構或涂改的話,“血緣”則是一種無法篡改的歷史傳承,王威廉意圖確認一種不遺忘的歷史記憶倫理。
《聽鹽生長的聲音》則站在靈魂的高度書寫了囚禁與救贖的主題。小說中,“我”和妻子夏玲居住工作于海拔3000多米的鹽礦區,朋友小汀帶著漂亮女友金靜順路過來見面。透過這個并不曲折的故事,作者提示著:我們都被囚禁于別人眼中的風景中。這是個由隱喻和象征結構起來的小說,隱喻中包含著對事物復雜性的理解。鹽湖的象征性就在于,它是每個人居處并渴望逃離的存在,卻又常常是別人眼中美麗的景致。因此被囚禁于鹽湖,幾乎是每個人存在論意義上的命定。然而,小說并不止于存在的荒涼,更包含著生命的救贖。當“我”更深入地觀照了他者生命的復雜性時,也突然了悟了死寂鹽湖的生命力——“我”終于能聽到鹽生長的聲音,“現在即使在喧囂的白天,我也能分辨出那種細碎的聲音”,“只有那不停生長的鹽陪著我”。鹽湖依舊,但“我”靈魂的光景已經大為不同。
荒誕、歷史和靈魂,是王威廉這些年寫作的關鍵詞,但這并非他的全部,他在散文和評論領域,也有諸多的創作,口碑頗佳。作為小說家,他渴望同時擁有務虛和務實兩套本領。作為作家,他渴望用一種“大文學觀”去打通文體的界限。他接下來的創作,值得我們繼續期待。 陳培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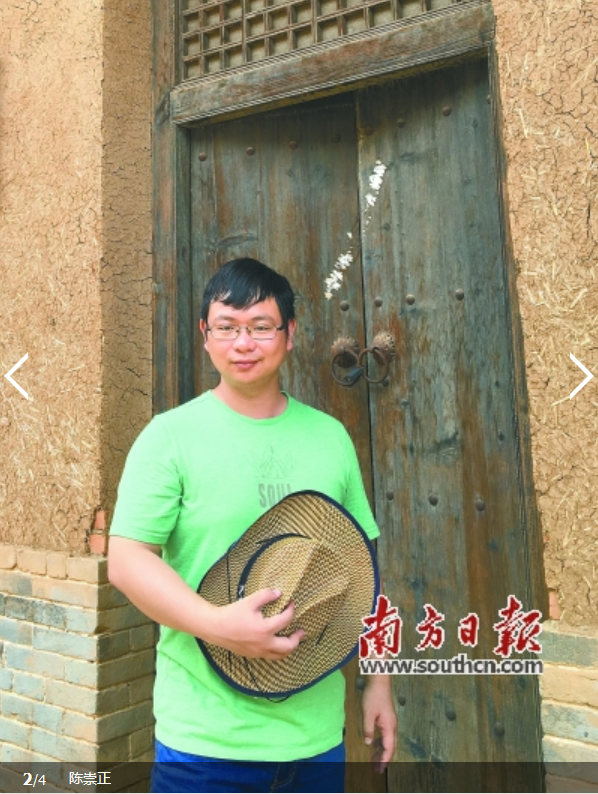
俠氣和真誠的小說家
——我眼中的陳崇正
陳崇正
1983年生于廣東潮州,曾在《人民文學》《收獲》等刊物發表作品;著有《半步村敘事》《我的恐懼是一只黑鳥》《正解:從寫作文到寫作》等多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文學院簽約作家,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創意寫作專業導師;現供職于《花城》雜志社。
阮雪芳
沈海高速潮州地段,一處開闊蒸騰之地——官塘,素以“魚生”和“牛肉火鍋”聞名。乍看這似一塊蠻荒野猛之地,疑懼此處民性彪悍,實則率直俠氣。從這里走出來的詩人小說家陳崇正,因襲了這種“俠”基因。
上世紀80年代末,每年端午前夕,少年陳崇正都會被父母派往山里看守自家竹林,以防竹葉賊偷竹葉包粽子而把竹筍踩碎,壞了一年收成。為打發竹林里漫長又無聊的時光,這個擅于自找樂子的家伙,削竹為器,自說自話,練就一套獨創的“內功心法”,那時他約摸十來歲,最大的理想是“練成絕世武功,寫在佛經里頭傳諸后人”,毫不知道這和屈原有關的節日所帶來的瑣事兒讓他得福,習武不成,倒冥冥中沾了文氣。
2006年,我在《他們帶不走詩歌和女人》中讀到他時,他已捆綁了笨重的行囊,勢頭獵獵,到東莞去混世界。韓山師范學院詩歌創研中心成立,他帶著他的女人和詩歌講稿回來參加,那是我和他第一次見面,灑脫、風趣,看去一副佛相,不語時厚實沉穩,笑起來卻明鏡拈花。講座上,他大談愛情、痛感寫作和朋友。陳崇正對朋友坦誠相見。2014年,他聽說我準備到廣州生活,一個電話撥過來,二話不說直奔主題,“住是首要解決的,到我妹家吧,這里還有一個房間”,接著還就新生活嚴肅地談了許久。是時,陳崇正也剛調到花城雜志社工作,暫住其妹家里。放下電話,一股溫熱直迫喉嚨。某次我遇事相托,表謝意,他輕松道:沒那么復雜啦,蹭了你好多餐飯。又拋來一句:加油,找個細丈讓我裝正經。小說家的嚴肅與天真讓人無比愜意。
朋友們提起陳崇正,都說這家伙出手快有才華有性情“活頭”得狠。
一次作家林淵液到省協學習,約了陳崇正、林培源和我小聚,他帶去《花城》雜志。當晚茶聊,他聲情并茂地談起摘香蕉之于寫小說的比喻,認為小說家寫小說和猴子摘香蕉一樣,是需要才華和天賦的。后來,這一說法作為趣味獨特的觀點“如何提高小說的完成度”,收入他的新書《正解:從寫作文到寫作》。
初夏深夜,讀他博客,貼的是小說集自序:邊緣的蒼老與復活。“我承認自己有過或曾有過寫作的才華,但在如蒸餾水的生活中,我明顯感覺到它正一點點地消失。這樣說起來或者有一些灰心喪氣,但卻無比真誠,一種蒼老的真誠……我凝望著,挪動著艱難的腳步。再過兩個多月我的孩子就要出生了,我想,我應該可以告訴他(她),這個父親一生探求的路上曾經有過不該有的彷徨。”看得我忽感心酸,夜色洇過的臉涼涼的,一抹都是淚。他平時顯露在人前的風趣幽默、云淡風輕,在這里,都收住了。可以說,那一夜,我才算真正了解結交多年的朋友。
我喜歡陳崇正的小說,他在魔幻與現實中設置了另一個平行空間,糅合著地理記憶、人文激活和情感喚起。離開故鄉多年,他沒有帶走那些美好的事物,相反,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直處于精神還鄉的狀態,如《半步村敘事》。這個打上烙印的文學地理符號,是他用文字構建與重返的精神故鄉。他將生活帶來的傷害,時代沖擊下的“宿命、恐懼、妥協、抵抗”,一一以事件展示,并企圖去理解和轉變為更為深邃的思考。如評論家陳培浩所說:“半步村在其筆下也從現實傳奇漸變為魔幻現實和民族寓言”。
至今,陳崇正已出版多部作品。往日竹林里的少年,將“內功心法”移情到對現實的關懷,被呈現的事物越分裂、絕望、逃離,觀察的頭腦就越集中、有力。他在與讀者直接對話的自序里,也從不遮掩內心的彷徨和焦慮、現實與理想夾層中艱難創作的體悟以及期許。他的小說《我的恐懼是一只黑鳥》,將恐懼寫到極致,小心翼翼的恐懼,是無法把握的災難感如影隨形,在人類共同的命運中,這種宿命意識,并不意味著能力不濟的妥協,而是呈現與理解背后的“抵抗”以及深沉的信仰。他說:“所以我要書寫恐懼,它才是勇氣誕生的源泉,它才是大多數人腳踩之處的質地”。
時代的聲音和影子漫過他的肩膀,他頭頂飛過的黑鳥正在飛,而世界上所有的黑鳥,都是生活核心負荷最重的原子,觸響生存縫隙間啞默無告的聲部。俠氣和真誠的小說家陳崇正,給黑鳥以豐翼,無論飛或者停歇,總有一個命運的拐點在那里,通往更加曠達而溫情的世界。

一個值得寄以厚望的小說家
——評皮佳佳小說集《方生方死》
皮佳佳
80后,廣東省文學院簽約作家,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美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已出版小說集《方死方生》,有小說、散文、古典詩詞發表在《收獲》《十月》《中國作家》《詩刊》《青年文學》《作品》《小說月報》等期刊。小說《方死方生》獲得2016屆廣東省有為文學獎。
皮佳佳是80后小說家,《方生方死》是她的中短篇小說集,在小說越寫越長、越出越多的今天,《方生方死》很可能因其細弱而湮滅在那些文字泡沫的海洋里。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有必要推薦一下皮佳佳的小說。皮佳佳的小說與當下80后的風尚寫作沒有任何關系,她既不同于“金錢奴隸制”的《小時代》,也不是淺嘗輒止的“意見領袖”。如果從譜系關系來說,皮佳佳延續的還是新文學以來的小說傳統。這是當下仍然被視為“正統”的小說傳統。這個傳統強調作家與生活、與社會的關系,強調對價值和意義的守護,強調人物的塑造和想象力的重要。這樣說,并不意味著皮佳佳就是一個年輕的“老派”作家。事實上,任何一個繼承新文學傳統的作家,由于個人閱歷和稟賦的不同,他們的小說創作一定帶有鮮明的個人印記。作為80后的皮佳佳也大抵如此。
中篇小說《彼岸天堂》,大體可以在“留學生文學”的范疇內來討論。只要有中西文化的交流,這一題材就不會終止。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都是留學生文學,但不同的時代背景賦予了這一題材遠不相同的內容和講述方式。一個叫林雅的女孩子,為了出國勉強嫁給了一個出身貧寒的“學霸”肖恩。但這遠不是“才子佳人”模式的古舊小說。林雅在屢次被拒簽后,終于幸運地通過了簽證,她如愿地來到了美國陪讀。但是“彼岸”并非“天堂”。兩個來自第三世界的青年,迅速被拋離了原來的生活軌跡。在兩種文明的邊緣,他們的現實生活捉襟見肘,情感生活分崩離析。令人尷尬甚至不堪的場景不斷被呈現出來。最后兩人終于還是分道揚鑣。當然,在當下的語境中,無論林雅還是肖恩,都說不上誰對誰錯。肖恩出身貧寒,他一直過著緊張的日子,他節儉地生活理所當然;林雅是一個北京知青的女兒,生活上要求多一點浪漫亦在情理之中。但是,在那個“彼岸天堂”,他們的青春和愛情,都在那險象環生的精打細算中付之東流。
我驚異于皮佳佳塑造人物的筆力。比如她寫來自山鄉的窮苦學生肖恩,一方面寫他的“城市化進程”相當緩慢并經常出現“不確定性”,一方面也寫出了這確實是一個吃苦耐勞的鄉村青年知識分子,日久天長的壓抑和以求一逞的焦慮,也終于異化了肖恩,這種異化是如此的徹底,幾乎浸透了他的靈與肉。
另一方面,皮佳佳在小說中非常注意景物描寫。現在的小說,為了抓住讀者,大多情節密不透風,很少有景物描寫。這樣的小說既沒有張弛有致的節奏感,也少有閑情逸致的趣味。但皮佳佳的小說注意到了這一點,她的景物、場景的描寫,都如期而至,讓讀者在既定的節奏內享受著悠然自得的起伏。這是皮佳佳小說特別值得肯定的方面。
《方生方死》的題材,對于皮佳佳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表面上這是一起針對底層妓女的兇殺案,一個名曰阿娟的妓女被殺了。作為專案組成員的女警察葉靈走進了這個案件和與這個案件相關的生活。小說在偵破、懸疑和正面書寫等不同角度穿插變幻。這不僅是個匪夷所思撲朔迷離的案件,重要的是,在偵查案件的過程中,通過葉靈的視野,我們看到了部分底層人的生存狀況。他們難以為繼的存活方式,決定了他們的精神狀況。《夜色無色》是一篇有強烈抒情意味的小說,當然也是一篇具有鮮明戲劇性的小說。余下的《罪愆》《阿公的心事》,也都別具一格。這里對日常生活的描摹和人物的狀寫,都相當有體會。我驚異的是,皮佳佳寫小說的時間并不長,而這里收錄的幾篇小說,卻都有不同的樣式,絕無重復或模式化之感。這實在是不容易的。我曾多次說過,一個中短篇小說家,最怕的就是結集——單看一篇小說時會感覺非常不錯;但如果結集后會發現,總會有程度不同的雷同之處。但皮佳佳這里沒有。僅此一點,皮佳佳就是一個值得寄以厚望的小說家。 孟繁華

詭譎之談,異稟之書
——讀林培源短篇小說集《鉆石與灰燼》
林培源
廣東汕頭人,80后作家,曾獲兩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在《花城》《作品》《青年文學》《香港作家》等文學刊物發表小說多篇。著有短篇小說集《鉆石與灰燼》《第三條河岸》等六部作品,新長篇《以父之名》即將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現于清華大學中文系攻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學位。
《鉆石與灰燼》所收錄的小說跟林培源以往的小說最明顯的區別是以異于現實常態的面相代替了象征、隱喻、變形等傳統的寓言化敘事策略。亦即所謂“異相”。換言之,通靈的白鴉、神諭般的菩薩對白、亦真亦假的燒夢儀式等《鉆石與灰燼》里的諸多“怪力亂神”本身就是作為現實的另一種面相出現在觀照范圍內,并簡單而機械地作為現實生活的符號指代。
在《鉆石與灰燼》中,“身體”不再單純地作為肉身的載體和性欲的表率,它是一套自成體系的修辭。它可以作為空間意義上的表述。《燒夢》里的一老一少,一個在異鄉漂泊歸來,一個還將漂泊遠方。身體在空間位置上的置換、調動與比照,也揭示出了身體曾經所在的歷史位置。與其說年邁的盛先生經歷了一次身體空間意義上的置換與調動,不如說他試圖將身體擱淺在記憶的空間維度上。記憶的空間占滿了歷史化的身體,現實的空間又無法安置沉重的肉身,于是盛先生選擇了燒夢儀式。燒夢儀式結束了,也就意味著身體游移出了歷史位置,具備了空間的選擇權。
身體同時也是靈與肉的熔爐,它的一端是咧嘴哂笑的欲望,另一端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與此同時,身體又是權力的主控。再以我認為可解讀面比較豐富的《家宅敘事詩》為例。祖父表面上是要通過養蜜蜂來寄托年老的生活。然而,這樣一份漫不經心的興趣愛好,實質上卻是關于權力的解讀——制造秩序。祖父年老,卻有著“心比天高”的意志,只是身體的老化和社會地位的邊緣,導致他不能再在自己的疆域里叱咤風云。他不為被蜜蜂螫傷的人道歉,他“從權力和欲望的大網上掙脫了,一轉頭掉入另一張網”。這張網表面上是養蜂這一興趣愛好,實質上是制造秩序的快感——他可以支配怎樣養蜂,他可以掌控蜜蜂的生死,他可以作為蜜蜂王國的君王。之后祖父被蜂群帶進蜂箱后的恐懼、孱弱與無能,儼然就是祖父在現實生活的投射——屈于人下,失去主控,拘于成規。相似地,《兩個葬禮與一場告別會》里那句“他的身體辭別了舞臺,心卻一直還在”也訴說了身體的權力意志。
《鉆石與灰燼》里,身體被控制、干預、改造、訓練與同構,被強迫完成不同的社會任務。但同時,身體又借由萌發的欲望和意外的神跡漸漸覺醒,由事件的主體轉變成社會的客體。
《家宅敘事詩》里的男孩出于好奇揪住女生的發夾。“她辮子上的綠色發夾像一只蜻蜓,振著翅膀引逗他”,不禁讓我想起畢飛宇《哺乳期的女人》中那個缺乏母愛且渴望母愛的留守兒童,他對惠嫂乳房的強烈期盼,一如林培源筆下的這個男孩對女生發夾的好奇。
人與人之間的理解是存在斷層的,所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秩序到倫理,從來就不是理想化的。而作家的任務不是霸道地以啟蒙者的姿態去修補這份斷層,而是以觀察者、經歷者的身份去觸及這份斷層。林培源筆下的男孩被父母訓斥懲戒,上下兩代的關系不是對話的,而是單向的;個體與群體之間的意識不是統一的,而是割裂的。在這里,《家宅敘事詩》的意義已經不在于異相的描寫,而是道出了人與人之間理解的斷層、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在男孩眼中,發夾僅僅是發夾,它是感官印象中的美好(迷人的綠色),它剔除了那些“男女授受不親”的規訓,它不存在猥褻與色情的界限。然而,這個發夾卻以“女生頭上的發夾”這一身份而存在,男孩的指尖已經不再是觸動了發夾本身,而是撩動了龐大的倫理觀念。這種分歧,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斷層。
從“異相”“身體”和“斷層”三個角度解構一部小說集這么血腥的事情我是比較少做的。然而,經過不斷的探索和尋思后,當林培源的小說開始“黃”起來、開始“暴力”起來、開始“幻化”起來的時候,側面印證了他的小說正是成熟起來的時候。在《鉆石與灰燼》中,敘事蛻變為作家與社會、作家與大眾、作家與自己的一場“事件”。縱觀《鉆石與灰燼》的諸篇目,那種以先行預設的理念來敘事的作者主控權漸漸隱去,取而代之的是不慌不忙的作者表述權。 劉漢波